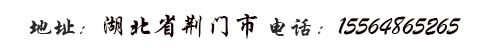三国衍生作品中,为啥有这么多神仙*怪
|
说起三国,许多人都会想到诸葛亮的“多智而近妖”。甚至,在不少人的印象中,诸葛亮就是个能“呼风唤雨”的奇人。 这个认知,显然与历史人物有很大的出入。可从三国题材的诸多衍生作品来看,种种神奇现象以及超出常人的事迹,却是非常普遍的。 不仅诸葛亮的“智慧”难以想象,就连不少武将,也绝非一般人。赵子龙能七进七出,张飞一言喝退百万曹兵,关羽手持八十二斤的青龙偃月刀,杀人如砍瓜切菜一样容易。 这倒还好,作为三国正史衍生作品中的巅峰之作,罗贯中的《三国演义》中,更是出现了很多“神仙*怪”,既有不可思议的法术,也有超出常人的神人。 一、小说《三国演义》中的神异描写 传统的“四大名著”,其实都带点“神仙”色彩。 《红楼梦》里,有贾宝玉梦游太虚幻境,也有绛珠仙草为了报恩而转世; 《西游记》不必多说,乃是古典神魔小说的集大成者; 《水浒传》同样如此,这里有神行太保戴宗的一日千里;也有宋江入梦,得到九天玄女传授的天书;更有入云龙公孙胜的正宗道法,帮助水泊梁山在战斗中无往而不利。 相较于前三者,《三国演义》虽然没有这么多神奇的人物、道法,但在它的每一个章节中,都获得或少存在一些关于神异之事的描写。 预言、星象、占卜、相术、谣谚、入梦、通灵、观星、天象、*神…… 三绝之一的“智绝”诸葛亮,便掌握着很多神异的本领。比如说相术,在见到魏延时,诸葛亮便立即看出这是一个“脑后有反骨”之人;又比如诸葛亮的未卜先知之能,庞统、周瑜、赵云等人的去世,皆有所征兆。 《三国演义》第五十七回提到: “孔明在荆州,夜观天文,见将星坠地,乃笑曰:‘周瑜死矣。’” 第七十七回中也有类似描述: “夜观天象,见将星落于荆楚之地,已知云长必然被祸。” 说到云长被祸,这里又正式提到了*神之说。在关羽遇害之后,其灵*竟然现身,帮助儿子关兴捉住了仇人潘璋;随后,在东吴的庆功宴上,吕蒙又被关羽的灵*附体,对着江东文武破口大骂。 类似的情节,还有于吉**向孙策索命的事情。 当然,除了这些“神仙*怪”,小说中的很多人物,也给予了读者一种不真实之感。最有代表性的,莫过于诸葛亮。 在“草船借箭”、“七擒孟获”、“空城计”、“死诸葛吓走活仲达”等一系列经典桥段中,诸葛亮“多智而近妖”的想象,给读者留下了深刻印象。 有了这些故事的铺垫,诸葛亮会未卜先知、能掐会算的神异本领,似乎显得不那么突兀。似乎在这个人身上,没有什么事是不可能的。 了解到这一点,其实就不难发现:小说《三国演义》中的一些“神仙*怪”,其实是裴松之注《三国志》的一种另类继承。 一方面,类似“空城计”、“死诸葛吓走活仲达”等故事,大多出自于裴松之的注解;而另一方面,裴松之的注解中,同样出现了不少“神仙*怪”的传说。 可以说,小说《三国演义》中的“神*”色彩,很大一部分便受到了裴松之注《三国志》的影响。 二、裴松之注《三国志》中的“神异”色彩 与小说《三国演义》一样,裴松之在为《三国志》补充材料时,便曾引用了大量的“神*异闻”,且主要分为两个部分。一个是带有“神*”色彩的传说,一个则是突出人物“特异功能”的记载。 比较有代表性的,是诸葛恪之死。按《三国志·诸葛恪传》注引《搜神记》记载: “恪入,已被杀,其妻在室,语使婢曰:‘汝何故血臭?’婢曰:‘不也。’有顷愈剧,又问婢曰:‘汝眼目视瞻,何以不常?’婢蹶然起跃,头至于栋,攘臂切齿而言曰:‘诸葛公乃为孙峻所杀!’於是大小知恪死矣,而吏兵寻至。” 其大概意思是说:诸葛恪在宫中被杀之后,他在家里的妻子却突然在婢女身上闻到了一阵血腥味,于是其妻便向这个婢女询问。这个婢女先是一呆,随后猛地一窜,就这么浮在了半空中,紧握拳头切齿道:“诸葛恪已经被孙峻杀掉了!” 值得注意的是,在《三国志》原文之中,一向惜字如金的陈寿,在描写诸葛恪之死时,也提前做了很多的铺垫。 诸葛恪进宫之前,其实遇到了很多怪事。比如,一个身穿孝服的人,莫名其妙出现在了诸葛恪的办公室;又比如,诸葛恪出征之时,中*营帐的顶梁柱却离奇断裂;后来,诸葛恪即将入宫,却又被家里的老狗咬住衣服…… 为了暗示诸葛恪的结局,陈寿先后记载了五件颇为离奇的事情。而裴松之所从《搜神记》中注引的这段材料,更是为诸葛恪之死增添了几分离奇色彩。 此外,小说《三国演义》中的梦验描写,也受裴松之注《三国志》影响颇深。 关羽发动襄樊之战,本是一帆风顺,可裴松之此时却注引《蜀记》,称关羽梦到了“猪啮其脚”,一时间,关羽也不自信了,反而对儿子关平说了一句“吾今年衰失,然不得还”。 与之类似的梦境,还有不少。孙权、孙策的母亲吴夫人在怀孕期间,曾梦见月和日入怀,此兄弟二人出生后,果然异于常人;曹魏谋士程昱入梦,见“泰山捧日”,疑似在暗指曹操有称帝之念。 更为荒诞离奇的是,裴松之还注引了一些“男人变女人”的案例。 按《三国志·周群传》注引《续汉书》:“建安七年,越巂有男子化为女人。” 又按《三国志·先主传》注引《蜀本纪》:“ 武都有丈夫化为女子,颜色美好,盖山精也。” 男人如何变女人?说起来,裴松之其实是想借这种荒诞之现象,来暗示王朝更替;但想要达到这种目的,裴松之能采取的办法有很多,而他,却偏偏选择了这种看似离奇荒诞的“神异故事”。 由此可见,裴松之对于“神*色彩”的异闻,带有明显的偏向与喜好。 除了上面提到的传说之外,裴松之也花费了不少笔墨来描写一个人的“特异功能”,在他的笔下,一些天才、异人、名将、相士、神医,都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有代表性的人物,除了前面提到的诸葛亮,还有赵云。赵云的“特异功能”,就是他几乎完美的人物形象。 实际上,《三国志》原文对于赵云的描写,的确有限。而真正将赵云捧上“完美武将”形象的,便是裴松之了。为此,他引用了《云别传》中的大量精彩描写,将赵云这个人物展现得淋漓尽致。 能看出来,裴松之对赵云非常喜爱,甚至用传统儒家的“五常”来要求这个人物,让他做到了儒家倡导的忠、义、仁、礼、智、信、勇。 赵云在公孙瓒麾下不受重用,刘备向他伸出橄榄枝,赵云莫不敢忘,在为兄长守孝之后,他按照之前的约定,不辞劳苦找到了刘备,此为“忠信”; 赵云入桂阳后,前太守赵范想要将嫂嫂送给他,赵云“固辞不许”,此为“礼”也; “益州既定,时议欲以成都中屋舍及城外园地桑田分赐诸将”,赵云据理力争,引霍去病“匈奴未灭,何以家为”之典故,劝说刘备打消了这个念头,此为“仁义”; 汉中之战期间,赵云固守营寨,却遇曹兵奇袭,千钧一发之际,赵云急中生智,反而广开营寨大门,上演了一场“空营计”,于是“曹*惊骇,自相蹂践,堕汉水中死者甚多”,此为“智勇”双全。 对于各种具有特殊才能的人,裴松之也非常乐于为他们增补许多事迹。 比如曹丕,除了能当皇帝,还擅长剑法、下棋。 按《三国志·文帝纪》注引《典论》: “尝与平虏将*刘勋、奋威将*邓展等共饮……因求(邓展)与余对。时酒酣耳热,方食芊蔗,便以为杖,下殿数交,三中其臂。” 又按《三国志·文帝纪》注引《博物志》: “帝善弹棋,能用手巾角。时有一书生,又能低头以所冠著葛巾角撇棋。” 此外,还有华佗的神奇医术、马钧的跨时代发明、夏侯荣的文思泉涌、杜夔的音律造诣、管辂的占卜与相术、葛洪的仙家本领,都让读者为之惊叹。 当然,这些神奇的人和事,到底是不是真实的,还有待商榷。 三、裴松之偏爱“神异”色彩的原因 上述可知,裴松之对充满“神异”色彩的人和事,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甚至在一些注引的材料中,能看出他有“猎奇”的心思。 这是让人感到奇怪的。毕竟,裴松之的作史态度一向是严谨的,还被人冠以“取材审慎,史德甚高”的美誉;而他为《三国志》注引的诸多材料,更是极大丰富、提升了这部史料的内容。 这样一位史学大家,为何独独偏爱这些看似荒诞离奇的材料呢? 从主观角度来看,裴松之所在的年代,还未出现科学的启蒙。受时代局限性所影响,大多数人对于一些“神异”之事,都持有相信的态度。 其实,无论是陈寿,还是裴松之,在选取史料之时,往往都会受到谶纬、五行、感性等学说的影响。 前文提到的“诸葛恪之死”,便很好说明了“因果报应”的道理。 按《论衡祸虚篇》记载: “世谓受福祜者既以为行善所致,又谓被祸害者为恶所得。以为有沉恶伏过,天地罚之,*神报之。天地所罚,小大犹发;*神所报,远近犹至。” 诸葛恪掌权时,不思进取,穷兵黩武,让不少百姓和将士苦不堪言。而他的遇害,正是在这种环境下发生的。 陈寿、裴松之不惜花费大量笔墨,用种种“神异”之事,提前为读者暗示了诸葛恪日后的悲惨结局,其实正是印证了汉晋年间广为流传的“因果报应”之说。 而从裴松之引用的诸多材料来看,对于一些“神异”事物,裴松之本人是相信的,而且,为了增强说服力,他还不惜查证了大量资料。 在《三国志·鲜卑东夷传》中,裴松之提到了一种神奇的马儿,因其身材矮小,主人骑着这种马,甚至能在果树下随意穿行。 于是,为了证明这种神奇生物的存在,裴松之信誓旦旦在后面说道:“臣松之按:果下马高三尺,乘之可于果树下行,故谓之果下。见《博物志》、《魏都赋》。” 再从客观角度来看,裴松之爱“神异”好“猎奇”的原因之一,也与当时的社会风尚有很深的联系。 从文学发展的角度入手,不难发现,魏晋时期的志怪小说,不仅仅是为了满足一部分人的猎奇心理,它更大的意义在于,能用一种新奇的方式,反映出真实的历史,这就是所谓的“用史笔写志异”。 对此,《隋书》中曾有解释: “魏文帝又作《列异》,以序*物奇怪之事,……杂以虚诞怪妄之说。推其本源,盖亦史官之末事也。” 在这些志异小说中,《搜神记》出场的评率当为最高。“考先志于载籍,收遗逸于当时”,尽管这本书收录了很多“神仙*怪”之事,但在某种程度上,它反映出了社会现实,以碎片化的方式,为后人展现出了一段段真实的历史。 因此,不仅是裴松之对《搜神记》有大量引用,其他史书诸如《晋书》、《宋书》、《后汉纪》、《续汉志》、《汉晋春秋》等,也对《搜神记》多有引用。 借志怪之事,写历史之实,恐怕只有在魏晋这个特殊时代,才能看到。 而身处这种环境下的裴松之,在作史时也难免受此影响。为了论证自己引用的史实,他采取一些神异之事,反而更能让人接受。 最后,还需要解决一个问题:为何裴松之要对一些具有“特殊才能”的人多著笔墨呢? 其实,这正是魏晋时期的士族,对于追求个性解放的真实写照。 随着玄学、道佛思想的兴起,儒家不在一家独大,因此它对人们的禁锢也大大降低。为了追求个性的解放、崇尚精神上的自由、进行认真的自我反省,越来越多的士族开始了“不务正业”,进而发展出了适合自己的特长和爱好。 裴松之出身于河东裴氏,乃天下之名的高门望族。在这样的环境下长大,裴松之并没有受到多少束缚,也没有像多数人那样钻研经学,反而一心做起了史学。 在他的心里,自己从事的这项爱好(或者说是工作),是非常有意义的;感同身受之下,裴松之对于一些拥有“特殊才能”的人,也自然多出了几分注意。 换言之,裴松之注《三国志》中提到的各方面“特殊人才”,其实也恰恰说明了:魏晋这个时代,是允许世人朝着多方面来发展的。 这不仅是一种赞许,更是一种鼓励。 参考文献:《三国志》注、《搜神记》、《论衡》、《隋书》 |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daxueteng.com/gjytx/8977.html
- 上一篇文章: 上古卷轴5的随从中不仅有美女,更
- 下一篇文章: 三国志战略版吊打司马盾三势吕2年嘟嘟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