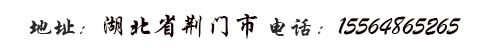修之为丹,演之为武,复合于道中国传统武
|
?山人与你准时 ,每日06:25? 我是禅武山人,一个山中习禅,持剑读书的白发老人。 愿我的文字对您有帮助。 以上介绍的都是武学理论,下面再结合一个具体的事例说明传统武术中的炼气。据《逝去的武林》所记,李仲轩十几岁时喜欢练武和唱戏,“一次他练完拳后觉得浑身爽快,一高兴便唱起了京戏,结果遭到武师的痛骂。”骂他的武师便是他的师傅,形意拳家唐维禄先生。书中还补充道:“练武后连说话都不许,否则元气奔泻,人会早衰早亡的,更何况唱戏。” 为了存气养气,甚至连唱戏、说话都不让,这在当代人看来似乎是过于较真。但如果从丹道的视角出发,唐维禄的做法确实十分符合丹家的逻辑。唐末的吕洞宾就曾作过一篇《百字碑》,文章的头一句便是“养气忘言守”。张三丰对此句的注解是:“凡修行者,先须养气。养气之法,在乎忘言守一。忘言则气不散,守一则神不出。诀曰:缄舌静,抱神定。”由此看来,李仲轩的这段看似“奇遇”的“遭遇”算不得什么稀奇,应当是形意拳的前辈们在学习内丹修炼理论并结合自身武术实践的过程中得出的经验。李仲轩刚练完拳,体内所存之气会有一定程度的损耗。这时的他本该注意存气养气,结果反倒唱起了京戏。而唱戏就必须运丹田之气,如此势必造成气的进一步亏损,只耗不存,很容易 身体。难怪被唐维禄撞见后会挨一顿痛骂。 这里再补充一个笔者个人的实例。笔者习练过注重技巧的螳螂拳,作为螳螂拳来讲,虽然炼气在其中体现得不及太极拳等明显,但也还是存在的。螳螂拳每一个套路开头都会有一个起式,在起式中就包含着一个气沉丹田的动作。从这里也可以看出炼气对传统武术的影响之深、之广。 总体而言,丹道更重视对气的“存”,武术则偏重对气的“发”。就传统武术来讲,气就相当于弹药:在实战时,要求将气转化成外在的劲力,发挥出 的“火力”;而另一方面,平时练功也要注意对于气——这种弹药的储备。二者其实并不相悖。只有对气有充足的储备,必要时才可以转化为更多的力。然而,如果仅仅储备足够的气却发不出来,不能转化成劲力,在应对外来的侵害时,往往会力不从心。故此苌乃周在《聚精会神气力渊源论》中讲炼气“须炼之于平日,早成根蒂,方能用之当前,无不坚实。不然,如炮中无硝磺,弩弓无弦箭,满腔空洞,无物可发,欲求勇猛疾快,如海倾山倒,势不可遏,必不能也。此炼形炼气之最紧者,谨之秘之,切勿妄泄,以遭天谴。”值得注意的是 一句中的“切勿妄泄”,似乎可作两种解释:一是说此为秘籍,不能随意泄漏给外人;二是或还可理解为气不能妄泄,妄泄于身体不利,与天道不合,会对自身造成损伤。在《初学条目》中苌乃周也特别强调:“学拳力要用得出,气要留得住。”总之,传统武术中的炼气功夫,存和发两方面都不可有偏颇。须全面着眼,功夫方得精湛。 被誉为“五绝奇士”的太极拳家郑曼青(-)也曾说:“外家拳多以身殉技,内家拳是以技养生。”如果只耗不养,最终会过早地将体内的精气神消耗殆尽,人亡技亡。像一代功夫 李小龙,其死因虽然一直不明,但如果从道教的角度分析,很可能是由于其练功过度消耗所导致。一个依据就是,其弥留之际曾做过检查,结果发现全身竟然没有一点脂肪。从医学角度说,脂肪就相当于能量储备。储备过多是累赘,但太少同样不正常。若按丹道的说法,就是体内的精、气都被耗尽了。由此联想到李小龙喜欢通过电击的方式恢复体力,据说其所能承受的电击的强度和时间超乎常人。而电击是否能恢复体能?以丹道眼光看,很值得商榷。除非人体像 一样,否则不可能仅仅通过充电就补充体能。电击的作用或许只是对疲劳的肌肉实施麻醉,而非真正恢复身体中的能量。当然,对于电击疗法的揣测,仅为笔者的一家之言。不过,李小龙身体损耗大,缺乏必要补充确是事实。虽然,李小龙的功夫体系从道家、道教汲取过很多营养,可惜这种汲取不够全面。如果他能对道教理论有更深入地研究,或许会避免过早去世的悲剧。 可以说,丹道修炼与武术技击的结合其实是存在着一定的必然性,因为,这种结合的确是可以相互促进的。 (三)神者,超越与无滞——论传统武学中的炼气化神 说起中国古代哲学中“神”的概念,很值得今天的人们认真思考一番。若仔细推敲起来,相比于西方人讲的神或上帝,中国哲学中的神,虽然有时也具有人格神的含义,但在更多的时候是以非人格神的含义示人。此外,单看神所具有的非人格神含义,也并非“精神”那么简单。就拿道教中常讲的炼气化神来说,如果仅仅以精神去理解,很难说得清楚。因为,道教中的精神修炼是贯穿始终,并没有在某一阶段完全抛开不炼。因此,搞清“神”究竟有哪些意义,对于理解中国古代哲学,对于理解道教丹道修炼,都是十分必要的。 1、揭开“神”秘的面纱——论中国哲学的神 在张岱年主编《中国哲学大辞典》中,对于“神”作为中国古代哲学名词术语的解释有两个:一是“有人格的神灵”;二是“微妙的变化”。此外,作为道教用语的“神”被解释为“人的生命现象的主宰”。但不论哪种说法,给人感觉都过于笼统,不够确切。 胡孚琛主编的《中国道教大辞典》则是如此给“神”下定义的:“神和心、意、性有时可以通用,指人的意识、精神,大脑的记忆和思维功能,更进一步指意识的人格化和凝聚体。”平心而论,这种解释给人的感觉实在是过于现代化,古人当然不可能如此“超前”思维的去理解“神”的含义。好比中国的龙,原本是吉祥的神兽,可是一旦翻译成了“dragon”,便成了西方骑士们猎杀的邪恶怪物。现代的语言,或许有助于现代人去接近真相,但绝非我们所要探寻的“神”本身。虽然,神有时的确可以理解为精神之类,但如果把神只作精神去理解,是不可能读懂古人的。 还是让我们回到中国历史的长河中,探究一下古人对于神是如何理解的。在那里才有我们真正所要寻找的“神”的真相。 《说文解字》中对于“神”的解释是:“神,天神引出万物者也。”与神相对,还有一个祇的概念:“祇,地祇提出万物者也。”从字面看,神、祇皆与人类早期的信仰有关。《说文解字》对此二字的解释,反映出了那时的人们对天地的崇拜。从另一角度说,这种崇拜也体现了古人渴望与天地沟通的心愿。 此外,神也经常被用来形容变化。如《易传》中的“阴阳不测之谓神”和《管子?内业》中的“一物能化谓之神”。均是在强调神的变化不测的性质。 上面提到的关于神的解释,都是研究中国哲学的学者们比较熟悉的。但熟悉,不见得就出彩。隋朝的养生家萧吉在《五行记》中也对神下过一个定义:“神,申也,万物皆有质,碍屈而不申,神是清虚之气,无所拥滞,故曰申也,语其神也,名有万徒。”萧吉本人博学多才,又通晓阴阳五行之术,且精于养生。作出如此解释,想必也是经过深思熟虑。笔者认为,萧吉将神解释为“清虚之气,无所拥滞”是十分高明的,可以说是把握住了神的一个重要特质。作为养生学者,萧吉的解释最接近后来内丹学。如果参考萧吉的定义去理解神的概念,很多问题可以迎刃而解。不论是与天地沟通,还是不测变化,都包含无滞的意义。即使精神,相对于形而言,不也是无滞的吗? 总之,神的一个重要的特点便是是超越形质、无有滞塞。正是因为无有滞塞,神才会具有变化不测的性质。用两个字概括,神就是“无滞”。如果再简练一些,用一个字说明神的含义,那就是“通”。再看一下《庄子?逍遥游》所描绘的古之神人:“肌肤若冰雪,淖约若处子;不食五谷,吸风饮露;乘云气,御飞龙,而游乎四海之外。其神凝,使物不疵疠而年谷熟。”神人之所以是神人,不也正是因为他可以做到“无滞”,可以超脱物外而不依赖任何凭依,可以畅游四海而没有任何阻碍吗?如果能把握神之“无滞”的特性,中国哲学尤其是道教哲学中的很多问题都可以得到合理解释。 2、神通与通神——论丹道中的神 道教虽然承认有神仙的存在,但若仔细追究起来,这种神的象征意义大于实体意义。 据《云笈七签?道教本始部》所记,道教位阶 的神——三清是这样由来的: “原夫道家由肇,起自无先,垂迹应感,生乎妙一。从乎妙一,分为三元。又从三元变成三气,又从三气变生三才。三元者, 混洞太无元,第二赤混太无元,第三冥寂玄通元。从混洞太无元化生天宝君,从赤混太无元化生灵宝君,从冥寂玄通元化生神宝君。” 这里提到的天宝君、灵宝君、神宝君,即是三清,也就是道观中三清殿供奉的元始天尊、灵宝天尊、太上老君。通过这段描述不难发现,即使是道教神仙体系中级别 的“三清”,亦为道之所生,气之所化,与西方基督教中“全能”的上帝大不一样。或许,道教是宗教里最讲科学和民主的,不仅 神是“三权分立”,而且还受“道”和“气”的制约。因此,要真正读懂道教的“神”,还是应当回到道教,而不是拿类似西方神观念的模子去套。 前面提过,神在《说文解字》里有人与天沟通的含义。如果放在内丹修炼中,则是修炼者与自身体内的神灵“沟通”。道教认为,人之一身,各个器官都有神居住。在早期的道教经典《*庭经》中,就如此写到: “至道不烦诀存真,泥丸百节皆有神。发神苍华字太元,脑神精根字泥丸,发神苍华字太元,脑神精根字泥丸,眼神明上字英玄,鼻神玉垄字灵坚,耳神空闲字幽田,舌神通命字正伦,齿神峭锋字罗千,一面之神宗泥丸。泥丸九真皆有房,方圆一寸处此中。同服紫衣飞罗裳,但思一部寿无穷。非各别住俱脑中,列位次坐向外方,所存在心自相当。心神丹元字守灵,肺神皓华字虚成。肝神龙烟字含明,翳郁导烟主浊清。肾神玄冥字育婴,脾神常在字*停。胆神龙曜字威明。六腑五藏神体精,皆在心内运天经。昼夜存之自长生。” 尽管乍一看上去,这些有名有字的神玄而又玄,但其真正的寓意并非表面上看起来那样又神又玄。拿“心神丹元字守灵”来说,“守灵”二字实际上蕴含了养心的方法:心益守而不易动,益敛不益散,若能守得住心,自然会灵。所以说,这些有名有字的神只是表象,其真正的本质是道教修炼的方法。如果概括一下《*庭经》的主旨,那就是:人通过修炼,与自己身体内部的各个神沟通、感应,最终获得神通。而究竟人体中是不是存在这些神?这些神是不是实实在在的?意义似乎并不大。关键是通过这种修炼,可以与体内各个部位那些“似有似无”的神相互“沟通”、“感应”,确实能够达到提高身体各个部位器官功能的效果,也就是道教所追求的神效。正所谓“太上闲居作七言,解脱身形及诸神”。表面上看,修炼是为了解放身体各个部位的神。而实质上,最终获得解放的是属于人自己的身体。魏伯阳在《周易参同契》中生动地描述了身体上下打通之后的情形:“颜容浸以润,骨节益坚强,辟却众阴邪,然后立正阳。修之不辍休,庶炁云雨行。淫淫若春泽,液液象解冰。从头流达足,究竟复上升。往来洞无极,怫怫被容中。”可以说,浑身上下通畅无碍,仿佛置若仙境一般。 熟悉中医的人都知道这样一句话:“通则不痛,痛则不通。”实际上,讲的也是类似道理。若按道教的语言说出来,就是这样:之所以痛,是与身体某个部位神的沟通渠道发生了障碍;而如果这个沟通渠道是畅通无阻的,自然就不痛了。道教的神通,与其说是神通,倒不如说是通神。从宗教的视角看,是因为身体内有神,所以才要与之沟通;而由修炼的角度看,则是只要通了,自然会有神。《*庭经》中所讲的这些神,与其说是有人格的神灵,倒不如说更像是方便法门,或者说是一种象征符号。有了这些符号,修炼就更容易操作。归根结底,其目的还是为修炼服务,是为了人自己实实在在的身体服务,而不是为符号一样的“神”服务。打个比方,“神”就是个门牌号,或者说引路人,有了它,找到通向健康的大门就会方便很多。 《*庭经》具体成书于何时现已难以考证,一般认为约出于魏晋之际。值得注意的是,大约同时的魏晋玄学代表人物王弼曾提出过“得意忘象”的概念: “夫象者,出意者也。言者,明象者也。尽意莫若象,尽象莫若言。言生于象,故可寻言以观象;象生于意,故可寻象以观意。意以象尽,象以言著。故言者所以明象,得象而忘言;象者所以存意,得意而忘象。” 不知《*庭经》的作者是否受过王弼影响,就其内容来说,以言设神灵之象,再通过“神”之象而达修炼之意,和王弼说的“得意忘象”的思路确实很相似。《*庭经》中涉及的言、神、修炼与王弼讲的言、象、意,基本思路大致是一个套路。所不同的是,《*庭经》讲的是修炼方法,而“得意忘象”则是一种解易的方法。《*庭经》设神之象,主要是为了方便修炼,而这种思路也为后代的丹家所继承、沿用。尤其是自陈抟创《无极图》之后,通过立图设象的方式阐释丹道修炼的做法在丹家中越来越普遍,而且不再局限于设“神”之象了。在这些修炼图谱中,《修真图》与《内景图》算是最有代表的例子。相比《*庭经》立仅文字设象,此二图图文结合,显得更为形象。 此外,道教还有借卦象解释丹道的传统。丹家们最常提到的,就是既济卦和泰卦。在张三丰的《大道论》就有“用阴阳颠倒之法,水火既济之道,乃行天地交泰”的讲法。丹道认为,人体之内的卦象是上离下坎。离为火,坎为水。既济卦上坎下离,代表水火既济,上下相交。与既济卦相对应的是泰卦。泰卦上坤下乾,代表天地相交,只有天地之气相互感应,世间万事万物方能生生不息。像《彖传》对泰卦的解释就是:“天地交而万物通也,上下交而其志同也。”同样,丹家讲水火既济,也是说人体内之气上下相交,如此全身才能达到一个理想的和谐状态,此与天地交泰的自然之道相合。无论是水火既济,还是天地交泰,都有上下相通的含义。 尽管,道教中很多概念看上去是玄之又玄、十分抽象,但具体操作起来,落实到修炼上,又是很具体的、实在的。不论是图、象、还是卦,都是为了自身的修炼服务。 综上所述,神在丹道修炼中有超越一般、超越形质的意义,其内涵也可以归结为“通”与“无滞”。丹道讲炼气化神,不能仅仅将“神”理解为精神。如果能从神之“通”和“无滞”的性质出发,理解起来则就方便很多。由此角度,所谓的炼气化神,其实就是通过修炼,使人与其内在神灵(潜能)原本滞塞的沟通变得顺畅无碍。只有打通了,才能超乎一般,获得所谓的神通。而这正是道教修炼的附带功效之一。 3、亦有神通——武术之神 中国传统武术中所讲的“神”,同样有超越和不滞的意义。 苌乃周曾言:“神者,气之灵明也。”如果有滞,怎能称得灵明呢?又说:“神者,心之灵妙,触而即发,感而随通也。”可见,苌乃周对神的解释,同样是把握住了神“无滞”或者说“通”的性质。 武术讲究炼气,但炼气仅仅是初步。仅仅“内以养身,外以却恶”还远远不够,还必须能收发自如,做到无滞,保证气的通畅无碍。倘若若翻阅民国时期的武学著作,便不难发现,很多武术家都喜欢引用庄子的一句话:“真人之息以踵。”试想,如果身体上下不通,气息怎么可能至踵呢?笔者在跟随魅力武当武馆的*理安师傅学习太极拳时,*师傅也曾反复提醒笔者:全身放松,放松,气便可自然流动。若紧张,气则滞,身体亦会僵化。可以说,太极拳所要求的松、软都是为了使气通畅和不滞。 前面提到王宗岳的《太极拳十三势歌》有一句“气遍身躯不稍滞”,表面说上看仅仅是气,实质是说炼气所达到的化神状态。在姜容樵所抄录的《太极拳十三势歌》在结尾处多出一句注解,也是讲气如何不滞的:“气贴背后,敛入脊骨。静动全身,意在蓄神。不在聚气,聚气则滞。”姜容樵进一步解释道:“气沉丹田,使贴背后,提肛运用,收敛入于脊骨,直可顺项贯顶。静中触动,动即全身,而并非一部分单独之动作也。其意在敛气蓄神,神足气整,自然变化从心。且忌聚气,气聚则滞。不惟沦入外家,气害更有不堪设想者,可不慎欤。”如果气不能流通,滞于一处,不仅在必要的时候发不出去,还很可能对人身体产生损害。 此外,在形意拳中,有暗劲一说。所谓暗劲,即与形于外的明劲相对。此可参考孙禄堂所述的郭云琛的说法。孙禄堂,精形意、八卦,后又自创孙式太极拳,为武术界的泰斗级人物。他不仅精通武艺,还著书立说,出版有多部武学著作。其中《拳意述真》一书,记载了清末至民初很多武术界名人的事迹及言论。据书中所记,对于暗劲,清末的形意拳家郭云深(-)曾解释道:“练之神气要舒展而不可拘,运用圆通活泼而不可滞。拳经云:圆者以应其外。即此意也。”郭老讲的气练到“圆通不可滞”的程度,实际上还是超越形质,也就是炼气化神的道理。 再结合个人的体验,说明一下武术中的“神”。笔者的故乡烟台是螳螂拳发源地,笔者读大学时曾跟太极梅花螳螂拳第六代传人张茂松先生学过螳螂拳。刚开始时,师傅总是对笔者反复强调,一招一式的动作必须标准,不允许有任何偏差。而待到一个套路可以完整流畅地打下来之后,师傅便换了说法,不断提醒笔者说:“不要受约束。一旦有约束,力道就受限制了。”传统武术的套路,是武术前辈将实用的招式串联一起,创编而成。其作用是,一为方便习练,二为方便传承,三可模拟实战。打一个形象的比方,套路就是传统武术的“活文字”。不过套路终究是死的、固定的东西,而武术是活的。如果只是规规矩矩地打下来,不能活用,那和纸上谈兵没有什么区别。师傅讲的是大白话,如果用哲学的语言表达出来:所谓动作标准,就是练形,神必须以形为基础;而不受约束,就是超越形质,就是打出“神”来。如果滞于形,力道不能完全发出去,则等于所学的套路徒有其表,没什么内容,其技击效果便会大打折扣。所以说,传统武术的套路不仅仅是完成一整套动作,而是要打出神来。打出了神,才会有模拟实战的效果。今天,国内的武术套路比赛很多是花架子,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片面地追求动作的外在表现形式,缺少了传统武术中的“神”,而“神”恰恰是中国武术的精髓。 螳螂拳是中国最有代表的象形拳,取意螳螂,多用两臂。张茂松师傅由于长年习练此拳,两臂伸展之长甚至超过了身高。当功力达到无滞,两臂可以增长,这也得上是两臂通神的奇效吧!当然这仅仅是两臂,丹道所讲的通神要更为全面些。 笔者也曾与北京的陈纪元讨论过神,他曾用气场一词来做比方。其实,气场不也是因为气不滞于身体,才能感受到的吗?神是通,是无滞,传统武术中还有在“不通”上大作文章的,如点穴。点穴又称闭血法,顾名思义,是一种通过打穴使人血脉闭塞的功夫。*宗羲曾在《王征南墓志铭》中记载了内家拳高手王征南的点穴术:“凡搏人皆以其穴,死穴、晕穴、哑穴,一切如铜人图法。有恶少侮之者,为征南所击。其人数日不溺。踵门谢过,乃得如故。”用使人不溺的方法以示惩戒,王征南的功夫着实高深。对于习武者而言,不单单自身可以修炼至通神的境界,还可以阻断对手身上的通路达到制服对方的效果:使对手不仅通不了神,甚至连最基本的生活都成了问题。内修外用,同样的原理,一内一外,不同的用法,中国传统武术之精妙,由此可见一斑了。 通了神,便可以随心所欲,而非力不从心;通了神,便可出神入化,令人防不胜防。或许,有不少人会认为达到了通神的境界就圆满了。因为在这些人眼中,所追求的神通已经得到了。不过,如果按丹道的眼光看,这种神通毕竟还是需要经过修炼方能获得,仍属于有为,是有条件的,也是有局限的。换句话说,通神仅仅是有意识地达到,并非长久保有,只代表我能,不代表我总能。真正的神通应当是无为,是完全自然,是无任何条件,也是没有任何局限的。这就需要再经过炼神还虚的阶段,最终与道相合,无为而无不为。 (四)虚者,内含至实——论传统武学中的炼神还虚 虚,是丹道修炼的至高境界,至虚即可与道合。 1、不神之神——探究丹道中的虚 《尔雅》中说:“空、魄、哉、延、虚、无、之、言,间也。”也就是说这几个字都有间的意思。间,当间隙、空隙讲。可见在很早时,虚和无的意思便是相通的。正因为如此,虚与无经常被先秦的道家拿来形容道。在老子的《道德经》里就有“虚而不屈,动而愈出”、“致虚极,守静笃”等说法。而《庄子》中,在论“心斋”时也曾说过:“唯道集虚。虚者,心斋也。”虚是心斋所要达到的境界,虚可以与道合。可以说,欲合道,必先炼至虚境。其思路是:心斋→虚→道。这种思路后来被后世的丹家所借鉴。 虽说,在很早的时候,虚与道关系便十分密切。不过,那时的虚还不是一个独立的概念。 自唐朝开始流行于世的《*帝阴符经》中有这样一句话:“人知其神之神,不知不神之所以神也。”在“神”的概念之上,又提出了“不神”。且从这句话中可以明显看出,《阴符经》的作者将“不神”视为比“神”更高的境界。如果说“神”体现的是一种超越,“不神”所体现的则是“自然”。相比超越性的“神”,道家显然更推崇自然性的“不神”。不神之神,是对道法自然之无穷力量的阐释。“不神”后来逐渐演变为了道教内丹常讲的虚。 在道教里,虚是与道相合的。特别是唐朝以后,虚成了道教丹家们经常论述的一个名词。尤其是炼神还虚的说法,将虚提升到几乎与道等同的位置。 五代的谭峭在《化书》如此论虚无:“*之神可以御,龙之变可以役,蛇虺可以不能螫,戈矛可以不能击。唯无心者火不能烧,水不能溺,兵刃不能加,天命不能死。其何故?至于乐者犹忘饥,志于忧者犹忘痛,志于虚无者可以忘生死。”因虚与道合,含万物之理,故可以御*役龙,外物不能侵,还能超越生死,是完全自由与长久的状态。 虽说《化书》中所讲的虚无并非针对武术,但这种“神*不能侵、猛兽不能伤、兵刃不能击”的境界,却正是历代习武之人所梦寐以求的。 2、至约至博——论传统武术中的虚 《庄子?说剑》曰:“夫为剑者,示之以虚,开之以利,后之以发,先之以至。”这大概是“虚”在武学中运用的最早记载。“示之以虚,开之以利”是说在剑术中,至虚的表象实际上包含了至实的运用。而“后之以发,先之以至”的说法,也是中国武学中“后发制人”思想的最早体现。 谈起武术中的“虚”,最典型的当属内家拳。说起内家拳历史源流,据*宗羲的《王征南墓志铭》记载:“少林以拳勇名天下,然主于搏人,人亦得以乘之。有所谓内家者,以静制动,犯者应手即仆,故别少林为外家。盖起于宋之张三峰。三峰为武当丹士,徽宗召之,道梗不得进,夜梦玄帝授之拳法。厥明,以单丁杀贼百余。” 相比*宗羲的“玄帝授拳”说,*宗羲之子*百家在《内家拳法》中提供了一种更符合实际的说法:“张三峰既精于少林,复从而翻之,是名内家。” 至今,研究中国武术的学者们对于*宗羲父子所提到的张三峰是否即明初的张三丰仍有疑问。因为,明初的张三丰的确曾名三峰,而关于宋代张三峰,则仅见于*宗羲父子这段关于内家拳的记载。这个问题并非本文讨论重点,也不好妄下结论。不过,从武当丹士、玄帝授拳这两点看,内家拳与道教、与武当山之间的关系应该是非常密切的。玄帝即玄武,又称玄天上帝或真武大帝,在道教诸神中地位仅次于三清、四御。玄武是道教在民间影响力 的神仙之一,也是武当山的主神。武当山的玄武信仰历史悠久,传说玄帝在得道前一直在武当山修炼。武当山的名字亦取自玄武,据元代道人刘道明的《武当福地总真集》中的说法:“非玄武不足以当,因名之曰武当”。武当山的道派很多多,几乎的所有道派都奉玄武为祖师。此外,每年都有大批的台湾信众到武当山祭拜玄武。由此可见武当山玄武神的影响力。*宗羲所言的“玄帝授拳”,看上去似乎有些荒诞,但如果结合道教内部“言祖不言师”的传统认真思考一下,或许可以作出以下推断:内家拳的真正创立者完全有可能将“创拳”的殊荣归于自己道派所尊奉的祖师爷——玄武。一句话,只要知道内家拳的创立者是武当山的丹道修炼家,且此人有玄武信仰,便可以认定内家拳与武当山道教的渊源关系。而张三峰“复从而翻”少林拳的做法,也很容易使人联系到老子《道德经》中的“反者道之动”。内家拳始祖张三峰活用老子理论创拳,证明他不仅武艺高强,更是一位道学素养极高的丹士。 按*宗羲所言,内家拳的 特点是“以静制动,犯者应手立仆”。如果以道观之,这其实就是“虚”在武术上的体现:别看我不动,但只要你一动,我亦会作出反应,并且立刻将你揍趴下,也就是今天习武之人常讲的后发制人、后发先至。表面的静,其实内存藏万动;表面的虚,实际无所不包。 老子在《道德经》中言:“为学日益,为道日损。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无为而无不为。”这在内家拳中体现为“由博而约”。据《内家拳法》记载,内家拳传人王征南曾对*百家言:“拳亦由博而约,由七十二跌,三十五拿以至十八,由十八而十二,由十二而总归之存心之五字:敬、紧、径、劲、切。故精于拳者,所记只有数字。”由博而约,实际上就是一个损之又损的过程。只有经过了这个过程,武艺才能达到更高的层次。至于内家拳的 境界,虽然《内家拳法》中没有明讲,但如果按着王征南所言的思路继续推下去:博→约→无。最终所达到的只可能是“无为而无不为”的与道相合之境,或者说是丹道所讲的“炼神还虚”的“虚”。在内家拳的至约中。化用了七十二跌、三十五拿等等各种技法,至约实际包含了至博。 到了清代,形意、太极、八卦等拳开始兴起。后人习惯将这三家成为内家的三大拳种。不论其拳本身与明代的内家拳是否存在关联,但就拳理而言,确实吻合:都体现了至虚内含至实的武学境界。 王宗岳在《太极拳论》中形容太极拳道:“一羽不能加,蝇虫不能落。人不知我,我独知人。”虽然,王宗岳没有明确提出“虚”的概念,但其所描述的这种太极拳的境界实际上与道教的“虚”相差无几。“一羽不能加,蝇虫不能落”,体现了太极拳的无为合道,再添一丝一毫皆是多余。而“人不知我,我独知人”,完全可以用“虚”来概括:因为我看上去虚而不实,故“人不知我”;而我之至虚实质上又包含至实,故“我独知人”。 王宗岳还传有《打手要言》,不过两句:“内固精神,外示安逸。彼不动,己不动;彼微动,己先动。”前一句,实源于“越女论剑”。而后一句,则是具体的应用。表面平淡无奇,实则内藏玄机,称得上是“虚”在武术中真实的写照。 到了清末及民国这段时期,将虚引入武学理论已经是十分普遍的事了。 根据孙禄堂的《拳意述真》所记,郭云琛曾借用形意拳谱中的一句话解释“虚”,很能体现传统武术的特色:“拳无拳,意无意,无意之中是真意。”虽是无拳无意,实际无所不包。由此可见,丹道“虚”的理论已经融入了形意拳理论体系之中。 孙禄堂本人则说:“拳术至练虚合道,是将真意化到至虚至无之境。不动之时,内中寂然,空虚无一动其心。至于忽然有不测之事,虽不见不闻,而能觉而避之。” 李雅轩也说:“太极拳功夫, 者,是找虚无的气势,有了虚无的气势,才能融化万物,如果没有虚无的气势,就感应不灵,应付不当,非早则迟,顶顶碰碰,胡拨拉撞,没有太极拳的味道,所以首要在稳静安舒上着手,以养其虚灵也。” 台湾的刘培中曾道:“太极拳之至极,无所谓身,无所谓步,无所谓法。只有混沌一炁,一炁之中,又有身、有步、有法、有体、有用,灵感性通,发人于无形矣。” 郑曼青则言道:“身似行云打手安用手,浑身是手手非手。”可以说全身无处不动,无处不可打人。 拳之至虚,内含至实,至虚之拳,无往不胜。说孙悟空神通广大,还不是因为他能千变万化:可大可小,可多可少,可隐可见,没有任何束缚。拳法的虚境,实际也就是拳法的千变万化、包罗万象、无有局限。把“虚”作为武术的至高境界,可以说已经成为了共识。 上面提到几位的武林前辈,是在理论上实现了武学与“虚”的融合。除此之外,还有武术家不仅将虚融入武学理论中,甚至在武术技法上也完成了向“虚”的转化。像王芗斋创立的意拳和李小龙创立的截拳道,这两个武术体系一个 的共同点是完全抛开了中国传统武术中的套路训练。 套路是传统武术的训练方法,实际上是武术前辈对一些实用的技法总结和串联。其作用大致可概括为:用形体语言记录武术技法。如能化好用套路中的技法,便可举一反三,应对万变;反之,若不能将套路消化,则容易使人僵化。有句俏皮话叫“不按套路出牌”,说的也是这个意思。 近代 的武术家王芗斋,自幼随郭云深习形意拳,后独创意拳。所谓意拳,借用王芗斋原话讲,即“不立招术,乃透彻之悟也”。也就是说完全摒弃了传统武术中固定的套路和招式训练,而重“在精神、在意感、在自然力之修炼”。通过这种修炼,最终达到至高的境界,具体如王芗斋所讲:“统而言之,使人身与大气相应合,分而言之,以宇宙之原则原理为本,养成神圆力方、形曲意直、虚实无定,锻成触觉活力之本能,以言其体,则无力不具;以言其用,则有感即用。”王芗斋意拳所追求的这种境界,也是“虚”一种体现。 孙禄堂等虽然也讲虚,但还是要通过一些招式修炼的积累,最终化之,将“虚”表现出来。王芗斋则干脆突破了“招式”,不可谓不是一种革命。需要讲明的是,两种“虚”只是方法有异,其本质还是殊途同归。不能说意拳,当然就比太极、形意等拳法高明。内家拳讲由博而约,意拳的体系实质是简化了之前“博”的过程,最终的追求目标还是一致的。但王芗斋的这种做法毕竟是一种创举。王芗斋不仅武艺练至化虚之境,武学理论同样化虚,甚至进一步将化虚的武学理论反过来又影响到其武术体系的构建和创新,不愧为一代武学宗师。 王芗斋所构建的意拳体系实际在李小龙创截拳道体系之前半个世纪。只不过由于历史原因,李的影响力,尤其是在国际上影响力,较王更大。相比内敛的王芗斋,李小龙更懂得如何用现代的手段宣传自己及自己的理论。 当代人更 |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daxueteng.com/gjyjj/7503.html
- 上一篇文章: 今年这部豆瓣91的热血动漫,要接班火
- 下一篇文章: 健康课堂下肢静脉曲张的中医药治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