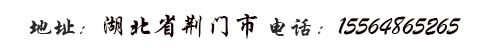历法与乐律相交下的产物
|
首发知乎 一、律历浅述 从汉代开始,一些历时较为长久的朝代几乎都在其正史中撰有《律历志》。班固的《汉书》是 本记述有《律历志》的史书,在此之前的史书都是将乐律与历法分为两个部分,他将《史记》中的律书和历书合并,创造了《律历志》,放在诸志 位。从此兴起了持续长久、跨代绵延的律历合一思维,《后汉书》、《晋书》、《宋书》、《魏书》、《隋书》、《宋史》中也有律历志。 新旧《唐书》无此志,元、明、清三代正史也无此志。但是,明代的落魄王子朱载堉的早期著作中有《律历融通》一书,详细解释了律历两者间的关系。清代王仁俊辑也有《律历逸文》等等,记载了后世对律历志的看法。 所谓律历志,是历法和乐律相结合所诞生的新历法,既可以应用到日常生活中,也可以从中找到乐律的架构。律历志是将乐律与历法相配,以乐律为基础,在其数理之上造作的历法。而乐律在这种历法里,则是作为一种有着自己独特数学意义的标准来定义历法和计量单位,历法对人们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而将这两者联系到一起的根本在于数学,《四库全书术数》序纪晓岚对数学的定义为:“物生有象,象生有数,乘除推阐,务究造化之源者,是为数学。” 而之所以选择乐律和历法匹配,是因为其核心在于古人认为“律者,均布也”,在中国古代传统中,乐律除了具有审美的价值之外,更是一种*教的艺术。并且二者都可以应用在*治层面,乐律与历法在古代都曾有着*治层面的应用。如乐律出现音调、音高与记载不符,就认为是乱世。而历法如果不能准确预测到日月食等,也会被认为是不祥之兆。可以说,自三代以降,中国就确立了“乐以为*”、”历以为*治“的制度体系,即圣人托神道以设教。尤其是乐律,人事上可以与天地相沟通,影响人的情绪以及万物。*治上体现国家的状态,君主的圣明,作为天命的表征,并且可以应用到*事战争中鼓舞士气或判断胜负吉凶。 《左传·昭公二十年》:“先王之济五味,和五声也,以平其心,成其*也。声亦如味,一气,二体,三类,四物,五声,六律,七音,八风,九歌。” 《乐叶图征》:“夫圣人之作乐,不可以自娱也,所以观得失之效者也。故圣人不取备于一人,必从八能之士。故撞钟者当知钟,击鼓者当知鼓,吹管者当知管,吹竽者当知竽,击磬者当知磬,鼓琴者当知琴。故八士或调阴阳,或调律历,或调五音。故撞钟以知法度,鼓琴者以知四海,击磬者以知民事。” 《乐记》:“治世之音安以乐,其*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宫乱则荒,其君骄。商乱则陂,其官坏。角乱则忧,其民怨。徵乱则哀,其事勤。羽乱则危,其财匮。” 《乐纬》:“声放散则*荒:商声欹散,邪官不理;角声忧愁,为*虐民,民怨故也;徵音哀苦,事烦民劳,君淫佚;羽声倾危,则国不安。”、“玄戈,宫也,以戊子候之。宫乱则荒,其君骄,不听谏,佞臣在侧;宫和,则致凤凰,颂声作。”又云:“弁星,羽也,壬子候之。羽乱则危,其财匮,百姓枯竭,为旱。” 《乐稽耀嘉》:“音安而乐其*平和,音怨而怒其*乖戾,音哀而思其*苛刻,音柔而荡亡国之征。” 《六韬·五音篇》曰:“武王问太公曰:‘律音之声,可以知三*之消息,胜负之决乎?’太公曰:‘深哉!王之问也。夫律管十二,其要有五音——宫、商、角、徵、羽,此其正声也,万代不易。五行之神,道之常也,可以知敌,金木水火土,各以其胜攻之。古者三皇之世,虚无之情,以制刚强,无有文字,皆由五行。五行之道,天地自然,六甲之分,微妙之神。其法:以天清净,无阴云风雨,夜半,遣轻骑往至敌之垒,去九百步外,偏持律管当耳,大呼惊之,有声应其来甚微。角声应管,当以白虎;征声应管,当以玄武;商声应管,当以朱雀;羽声应管,当以勾陈;五管声尽不者宫也,当以青龙。此五行之符,佐胜之征,成败之机。’武王曰:‘善哉!’太公曰:‘微妙之音,皆有外候!’武王曰:‘何以知之?’太公曰:‘敌人惊动则听之。闻抱鼓之音者角也;见火光者微也;闻金铁矛戟之音者商也;闻人啸呼之音者羽也;寂寞无闻者宫也。此五者,声色之符也。’” 《周礼·太师》曰:“大师执同律以听*声而诏吉凶。”郑注云:大师,大起*师。 《兵书》曰:“ 行师,出*之日,太师吹律合音,商则战胜,*士强;角则*扰多变,失士心;宫则*和,士卒同心;征则将急数怒;*士劳;羽则兵弱,少威明。” 《律书》曰:“六律为万事根本,其於兵械,尤所重焉,故云‘望敌知吉凶,闻声效胜负’,百王不易之道也。武王代纣,吹律听声,推孟春以至于季冬,杀气相并,而音尚宫。同声相从,物之自然也。” 《乐记》:“宫为君,商为臣,角为民,徵为事,羽为物,五者不乱,则无怗懘之音矣。宫乱则荒,其君骄。商乱则陂,其官坏。角乱则忧,其民怨。徵乱则哀,其事勤。羽乱则危,其财匮。五者皆乱,迭相陵,谓之慢。如此,则国之灭亡无日矣。” 网易云造就一批抑郁症,证明了乐律的强大(确信) 乐律,即音律,指音乐上的律吕和宫调,律便是十二律吕,各律制度从低到高依次为:*钟,大吕,太簇,夹钟,姑洗,仲吕,蕤宾,林钟,夷则,南吕,无射,应钟。又因为奇阳偶阴的思想,其中奇数各律(*钟、太簇、姑洗、蕤宾、夷则、无射)称“六阳律”或“律”;偶数各律(省略)称“六阴吕”或“吕”。总称“六律、六吕”。或简称为“正律”,乃对其半调(高八度各律)与倍律(低八度各律)而言。 这里我们还要讲一下十二律吕的来源,在《吕氏春秋仲夏古乐》记载:“昔*帝令伶伦作为律。伶伦自大夏之西,乃之阮隃之阴,取竹於嶰溪之谷,以生空窍厚钧者,断两节间其长三寸九分而吹之,以为*钟之宫,吹曰舍少。次制十二筒,以之阮隃之下,听凤皇之鸣,以别十二律。其雄鸣为六,雌鸣亦六,以比*锺之宫,适合;*锺之宫皆可以生之。故曰:*锺之宫,律吕之本。”根据这个故事我们可以知道,所谓十二律吕是用不同长度的竹筒所作。竹管长的声音低,竹管短的声音高,而其他十一律都是由*钟损益所起,由此确立了十二律吕,以分阴阳。 而历法自然就是为了配合人们日常生活的需要,根据天象而制订的计算时间方法。简单说就是根据天象变化的自然规律,计量较长的时间间隔,判断气候的变化,预示季节来临的法则。时间长河是无限的,只有确定每一日在其中的确切位置,我们才能记录历史、安排生活。不同的历法作用也不同,譬如阳历的二十四节气对于农事具有指导作用,而阴历因为本质在于朔望月所以对宗教活动和传统节日起到很大的影响。我们日常使用的日历,对每一天的“日期”都有极为详细的规定,这实际上就是历法在生活中最直观的表达形式。 《大戴礼记·曾子天圆》: “圣人慎守日月之数,以察星辰之行,以序四时之顺逆,谓之历;截十二管,以宗八音之上下清浊,谓之律也。律居阴而治阳,历居阳而治阴,律历迭相治也。”卢辩注:“厤以治时,律以候气,其致一也。” 《国语》: 景王问钟律于伶州鸠王将铸无射,问律于伶州鸠。对曰:“律所以立均出度也。古之神瞽考中声而量之以制,度律均钟,百官轨仪,纪之以三,平之以六,成于十二,天之道也。 乐律和历法,两者虽然都涉及到数学,并且都是天之道。但是本质上却风马牛不相及的。究竟是什么使得这两种不同的学科融合在一起,产生这种律历合一的思想,我们还要从三皇时期说起。(非实际三皇时期) 二、律与计量 早在三皇时期,人们就认为乐律、历法与长度、容量、重量即度量衡是相通的。以律吕为基底,既可以与历法相合,也可以制定度量衡。据《尚书虞书舜典》载,传说中的舜帝在巡视东方部落时曾下令“协时月正日,同律度量衡”。《吕氏春秋仲夏大乐》也有:“二曰:音乐之所由来者远矣。生於度量,本於太一。”《淮南子.主术训》进一步指出:“乐生于音、音生于律、律生于风,此生之宗也“这就是要求各部落应有统一的日月时间、相同的乐律与度量衡。所谓“同律度量衡,就是指统一了音乐、长度、斗斛、斤两的标准。 这种以乐数配度量衡数和历法数的思维,在《汉书律历志上》就有说明:“数者,一、十、百、千、万也,所以算数事物,顺性命之理也。”在《史记》中也有:“ 制事立法,物度轨则,壹禀于律。六律为万事根本焉。”可以看出三者间的互通是由于乐律,而根本原因在于基底都为数学,数术大则可以通神明,顺性命。小则可以经世务,就是这个道理。 还有的人则认为“同”代表着阴律,而“律”代表着阳律,所谓“同律”,实际上就是“十二律吕”的意思。古人将音乐视为上天的恩赐,对待音乐,极其的严谨。如《乐纬》就强化了圣王受命与制礼作乐的关联,解释了五声与五*比附模式的内在理据,并将八音乐器作为省察*治功效和构建社会制度的重要工具,《乐纬》维护统治的根本原因在于确立了制礼作乐的主体为“圣王”。在儒家的思想体系中,并非所有帝王都能制礼作乐,“虽有其位,苟无其德,不敢作礼乐焉;虽有其德,苟无其位,亦不敢作礼乐焉”。 儒家强调“ 功成作乐,治定制礼”,将礼乐制作视为表彰帝王功德和彰显教化的手段。但谶纬文献,却开始强化帝王受命和制礼作乐之间的关系,《乐叶图征》曰:“受命而王,为其制乐,乐其先祖也。”《尚书璇玑钤》也载:“使帝王受命,用吾道,述尧理,代平制礼,放唐之文,化洽作乐,名《斯在》。”《乐记》释作乐之起,在于人心感物,而“民有血气心知之性,而无哀乐喜怒之常”,故“先王(作乐)本之情性,稽之度数,制之礼义”。春秋时期“礼崩乐坏”和“礼乐文化”就是对此最有利的说明。董仲舒也说:“ 必受命而后王。 必改正朔,易服色,制礼乐,一统于天下,所以明易姓,非继人,通以己受之于天也。” 所谓“同律度量衡”,就是要像对待音律那样,慎重的对待“度量衡”,制定标准。两种对‘同律’的不同解读,最终的意思大致是相近的。只是前者更符合我们现代人的标准,而后者更贴切古人“阴阳五行”、“天人合一”、的思维方式。 这种统一的思想显然与农业生产、经贸与文化交流密切相关。然而,可惜的是在秦汉之前,各国之间标准不一。历法、乐律与度量衡似未曾在各国间真正统一过,秦始皇统一六国,才颁布诏书统一度量衡。汉初也仍旧沿用秦朝时体系,刘邦命令张苍根据秦制“定度量衡程式。”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西汉都继续沿用秦朝建立起来的包括律、度、量、衡在内的各项制度。度量衡这些计量单位的统一化、标准化。为国家之间的贸易、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律管一般简称为“律”或“管”。律管是用来发声的,但是声是无形的,要发声就必须规定出能发出*钟宫声的律管,并且它的长度、口径都是固定的,否则音的高低就会发生变化。这种变化人的耳朵一般都能感觉得到。要把有形之器定量化,就需要通过测量把发出固定音高的*钟律管的长度和口径记录下来,这样就可以确定一个可视的客观标准了。 而关于律与度量衡的标准,我们以《汉书律历志上》所载为准: 度者,分、寸、尺、丈、引也,所以度长短也。本起*钟之长。以子谷秬黍中者,一黍之广,度之九十分,*钟之长。一为一分,十分为寸,十寸为尺,十尺为丈,十丈为引,而五度审矣。其法用铜,高一寸,广二寸,长一丈,而分、寸、尺、丈存焉。用竹为引,高一分,广六分,长十丈,其方法矩,高广之数,阴阳之象也。分者,自三微而成著,可分别也。寸者,忖也。尺者,蒦也。丈者,张也。引者,信也。夫度者,别于分,忖于寸,蒦尺,张于丈,信于引。引者,信天下也。职在内官,廷尉掌之。量者,龠、合、升、斗、斛也,所以量多少也。本起于*钟之龠,用度数审其容,以子谷秬黍中者千有二百实其龠,以井水准其概。合龠为合,十合为升,十升为斗,十斗为斛,而五量嘉矣。其法用铜,方尺而圜其外,旁有BB31焉。其上为斛,其下为斗。左耳为升,右耳为合龠。其状似爵,以縻爵禄。上三下二,参天两地,圜而函方,左一右二,阴阳之象也。其圜象规,其重二钧,备气物之数,合万有一千五百二十。声中*钟,始于*钟而反覆焉,君制器之象也。龠者,*钟律之实也,跃微动气而生物也。合者,合龠之量也。升者,登合之量也。斗者,聚升之量也。斛者,角斗平多少之量也。夫量者,跃于龠,合于合,登于升,聚于斗,角于斛也。职在太仓,大司农掌之。衡权者:衡,平也;权,重也,衡所以任权而均物平轻重也。其道如底,以见准之正,绳之直,左旋见规。右折见矩,其在天也,佐助旋机,斟酌建指,以齐七*,故曰玉衡。《论语》云:“立则见其参于前也,在车则见其倚于衡也。”又曰:“齐之以礼。”此衡在前居南方之义也。权者,铢、两、斤、钧、石也,所以称物平施,知轻重也。本起于*钟之重,一龠容千二百黍,重十二铢,两之为两。二十四铢为两。十六两为斤。三十斤为钧。四钧为石。忖为十八,《易》十有八变之象也。 这里我们可以得到度量衡与十二律吕中*钟管长、容积、重量的对应关系。 长度有分、寸、尺、丈、引,他们起源于*钟的管长,用黑色中号的黍来测量,一黍的宽度是九十分,正好是*钟的长度。一个单位就是一分,十分就是一寸,十寸就是一尺,十尺就是一丈,十丈就是一引,这样五种测量长度的单位就明白清楚了。 测量容积的工具有龠、合、升、斗、斛,是用来测量多少的。本来起源于*钟的竹管,用长度的数字来确定它能容纳多少,用中号的谷子黑黍一千二百颗来装满竹管,用井水来让它平整。一*钟竹管的数量就是一合,十合是一升,十升是一斗,十斗就是一斛,这样五种量器就完善了。其中除二龠为一合外,其他均为十进制。 称量物体的单位有铢、两、斤、钧、石,它们是用来称量物体平衡的标尺,弄清楚物体的重量。本来起源于*钟的重量。一*钟竹管装一千二百粒黍子,重量是十二铢,十二铢的两倍就是一两。一两有二十四铢。十六两就是一斤。三十斤就是一钩。四钧就是一石。 这种“累黍定尺”的方法,简便易行,毕竟是常见的粮食,家家户户都可以采用。海昏侯墓中就发现了许多这种黍子,这里额外说一下,一般我们现在说的谷子指的是稻谷、麦子。但是在古代北方有五种粮食,也就是我们说的五谷:稻、黍、稷、麦、菽,黍去掉壳,就是*米可以酿酒、做糕。由于不利于消化,现在也基本上不用“黍”作为主食了。 黍是耐干旱的作物,它外表坚硬、不易损坏,不过它的品种很多,大小也有差异。如何能尽量选择每一粒黍正好与一分的长度相吻合更为重要。刘歆下令把各地的黍子都集中起来,又把它们分成大、中、小三等,分别排列,测量它们的长度、容积和重量。 终于得到了理想的结果,即某个品种中等大小的黍(可惜他没有提到用的是哪一个品种),一粒相当于一分,90粒黍即合*钟之长,粒黍当一尺;粒黍又正合*钟律管之容,与一龠相当;所容的粒黍之重量约略相当于12铢。 经过刘歆以黍定管的提议,终于巧妙地将律管、黍与度量衡三者联系起来。对度量衡与*钟、累黍的关系作了清楚的交代。度量衡与*钟律互为佐证,再以累黍为介质,相互参校,即可以记载于书,形之于物了。有了器物、有了数据,后人也就可以具体操作了。 而后世关于刘歆以黍定管的故事,也十分感兴趣。历史上最早验证这种观点的是荀勖。汉代末年,由于战乱纷扰,各种礼仪器物包括度量衡器大多已消亡,晋武帝时,令律历学家荀勖考证古乐律。荀勖凭着他丰富的乐律知识和聪慧的听力,判定当朝宫廷内的太乐八音不和。究其原因正是东汉至晋的尺度长了四分有余,尺度增长了,律管也随着加长,造成乐律失准。于是考证了各种古器并相互校验,终于制定了一支古尺,用此尺重定律管长度。后来经过证明,荀勖所定的古尺与古律都与秦汉时的尺度和*钟宫声完全相符。可见,律与尺相互校验是可行的。其后,李淳风在考证唐朝以前历代尺度时说:“以律度量衡,并因秬黍,散为诸法,其率可通故也”。他以“莽量尺”作为基准(列为 等),与他搜集的汉以后魏、晋直至隋,前后17个朝代,27种尺与 等尺作比较,分别按尺度的长短列为十五等,后来又被收入《隋书·律历志》,成为后人研究这期间一尺之长的重要历史资料。因此,“十五等尺”在度量衡史上也占有重要的地位。明朝对度量衡与乐律、累黍的讨论,主要见于朱载堉的《乐律全书》。他为了验证*钟律管、累黍的关系,甚至跋山涉水寻找合适的竹管,还亲自种植各种黍加以验证。 还是不得不承认在当时的条件下,找不到另外任何物体可以取而代之。清朝对前代尺度考订,主要是康熙、乾隆两位皇帝。康熙在考订*钟律和累黍时,亲自验证, 提出横累粒为古尺,竖累粒为清营造尺。他的这一做法十分巧妙,即把古制寓意在其中,还把清朝长32厘米的营造尺,也用累黍(竖排)的方法排列了出来。 由此可见,*钟之管的重要程度和今天的标准1kg重量球一样重要,是制定计量单位的 标准。而*钟管为竹子所作(海昏侯墓发掘出玉制*钟管,但是一般都是竹子),所以要求律管本身长度、容量必须一致,所发的声音不能有错误,管身不会因为气候、破损等原因出现问题,导致计量失衡。最初只能以音色判断管长是否符合标准,直到刘歆用黍子规定*钟管长之后,才使得*钟管长有形可检、有数可推。这种计量方法虽然后世已经弃用,但是仍为我们考察汉朝时计量单位提供了莫大的帮助。这既体现了《说文解字》中:“律者,均布也”的思想,也表明了律作为一种标准深入人心,正如朱载堉在《律历融通卷三律元》所说的:“律,法也。莫不取法焉,是为万事根本”体现了最初的法律制度思想。 代表1kg的金属球 法律 三、律与五声和天文易数 在文章开头我们说过,乐律和历法实际的联系点在于数学,推动这种联系的则是汉代由于*治原因,在这种神秘主义下的思想。那么数是什么?数学又是什么?我想我们在探究乐律与历法数理层面的关系时,这是一个无法绕开的话题。 《汉书律历志》:“数者,一、十、百、千、万也,所以算数事物,顺性命之理也。” 历代以来的谶纬术数家所追寻的高度正是秦九韶的《数书九章》所言:数学大则可以通神明,顺性命(京、焦,入于禨祥);小则可以经世务,类万物(陈、邵,务于造化)。 至于数学,秦在《数书九章》说: “周教六艺,数实成之。学士大夫,所从来尚矣。其用本太虚生一,而周流无穷,大则通神明,顺性命;小则可以经世物,类万物,讵容以浅近窥哉?” “今数术之书,尚余三十家。天象历度,谓之‘缀术’,太乙壬甲,谓之‘三式’,皆日内算,言其秘也。 《九章》所载,即周官‘九数’系于方圆者,为‘专术’,皆曰外算,对内而言也。其用相通,不可歧二。” 由此可见,这里将数学明确地分为了两部分。其中“内算”大体就是指“术数”,《四库全书》也将易数等称为内算,附会易数的称为小数。内算主要指天文、历数、太乙、六壬、奇门遁甲等;而“外算”则接近现代意义上的“数学”,这里只是将数学分为两个体系,需要注意的数学根本在于数的运算法则和应用层面,正如《九章》所载。现代对于传统数学发展之研究,多是侧重于其运算的方法和技巧。 再绕回来,前文说到乐律是有自己的数学模式,律历志的历法就是在此数学模式之上建立的。而最初律历的数是和天文易数相配,最终反过来为历法做根基。律吕可以与节气、月份、星宿、季节、五行、时辰等相配合。而之所以可以产生这种配合的原因在于天人思想,较为明显的是通过律管吹灰来候气的方法。(这里额外插一句,后世的律吕择日法,完全是想当然所作,先定年然后按隔八生律推月,从月推日,从日推时,自谓取生生不息,百无禁忌。实际上这种择日法没任何用,反而容易出凶煞。) 古人认为每个节气都有所不同,通过不同律管的飞灰可以推测节气具体来临的时间,这个也和邹子吹律改变天气,以及孔子吹律定姓的故事有所关联,《白虎通·姓名》:“圣人吹律定姓以纪其族。”陈立疏证引马驌《绎史》:“圣人兴起,不知其姓,当吹律定声以别其姓。”又引惠士奇《礼说·世奠系鼓琴瑟》:“司商,乐官也。人始生,吹律合之,定其姓名。”源自于早期对于乐律的神化和延伸。 唐代韩偓《冬至夜作》诗里说,“中宵忽见动葭灰,料得南枝有早梅。”葭灰,也叫葭莩之灰。葭是指初生的芦苇,葭莩是指芦苇杆内壁的薄膜。古人烧苇膜成灰,置于律管中,放密室内,以占气候。某一节候到,某律管中葭灰即飞出,示该节候已到。 沈括的《梦溪笔谈·象数一》引晋司马彪《续汉书》:“候气之法,於密室中,以木为案,置十二律琯,各如其方,实以葭灰,覆以緹縠,气至则一律飞灰。” 蔡元定在《律吕新书卷二·律吕证辨》中说:“今欲求声气之中而莫适为准则,莫若且多截竹,以拟*钟之管,或极其短,或极其长,长短之内每差一分以为一管。” 这种以律侯气的方法在先秦时期还完整保留,但是秦始皇焚书坑儒以后曾一度失传。后来由汉代的易学家、乐律学家京房(本名李君明)独得真传。而京房这个名字就是李居明吹律所定,《京房传》说他“好钟律,知音声”。四库馆臣认为,由于京房独得“候气”之奥秘,又师承易学一代宗师焦延寿,受学六十律上下相生之法,所以成为了 易学家和乐律学家。 而宫商角徵羽五声,也就是宫调的由来,也和*钟有关。《汉书·律历志》说*钟为天统,又说:“五声之本,生于*钟之律。九寸为宫,或损或益,以定商、角、徵、羽。”也就是说,宫、商、角、徵、羽五声都是由*钟派生出来的,如果把长九寸的*钟律管发出的声音确定为宫,那么,减少或增加律管的长度,便形成商、角、徵、羽。这就明白无误地告诉我们,*钟之律作为宫,是最基础的也是最重要的,其他声音都是由宫决定的。正如《汉书·律历志》所说,“宫,中也,居中央,畅四方,唱始施生,为四声纲也。”“*钟 ,亡(无)与并也。” 其次,十二律也是以*钟之律为基准的。《汉书·律历志》指明,是按照“三分损益”法确定的。在《管子地员篇》就可以看到,具体地说,三分损益就是以*钟九寸之长为准,“三分损一,下生林钟。三分林钟益一,上生太簇。三分太簇损一,下生南吕。……” 京房把传统的十二律扩展成了六十律。也就是上面说的三分损益法,是“以上生下皆三生二,以下生上皆三生四”用这种方法,当生到第十一次(即第十二律)后,不能回到出发律上,使得十二律不能周而复始。对此,京房采用了扩展十二律的解决办法。根据传统的三分损益法,*钟生林钟,林钟生太簇,太簇生南,这样依次相生, 是无射生中吕,就得到了十二律。 京房从中吕起继续往下生,直到六十律为止。其实,六十律并不是京房的发明,《后汉书律历志》明确记载汉元帝派人向京房问律,“房对受学故小*令焦延寿六十律相生法”。可以看出,京房所得的六十律相生法,是源自于他的师父焦延寿。 汉书将十二律三分损益称为隔八生律,(尽管王光祈先生认为这是进八退六律),在一个八度内排布十二律,因京房规定了“下不过清*钟,上不过浊*钟”,三分损益导致每个新音律都是原来音符的2/3倍,或者4/3倍,而返宫却要回到八度,也就是2的整数倍。2/3和2的关系无法调和。因此第七律蕤宾之后继续上生得到大吕。 十二律三分损益过程如下: 十一月*钟81以上生下皆三生二得到林钟六月林钟54以下生上皆三生四得到太蔟一月太蔟72以上生下皆三生二得到南吕八月南吕48以下生上皆三生四得到姑洗三月姑洗64以上生下皆三生二得到应钟十月应钟43以下生上皆三生四得到蕤宾五月蕤宾57以上生下皆三生二得到38,由于38低于清*钟40.5因此蕤宾不能以上生下,而只能继续以下生上五月蕤宾57以下生上皆三生四得到大吕十二月大吕76以上生下皆三生二得到夷则七月夷则50以下生上皆三生四得到夹钟二月夹钟67以上生下皆三生二得到无射九月无射45以下生上皆三生四得到中吕,四月中吕60极不生 尽管古代还有其他的生律法,但通常不做备注的情况下十二律三分损益六十律三分损益都是“蕤宾重上法”之后,历代正史对“候气之法亦屡有记述。但其细节说法各异,正如明代学者朱载商所盲:“候气之法各有异同,总似道听途说......面未尝试验耳” 事实上,从六十律问世起以至后来,就音乐实践而言。京房六十律确未有过实际的影响或指导作用。他在乐律学的成就一方面来自于其师焦延寿,另一方面是来原于他的易学造诉和他对阴阳五行原理的深刻理解。 《后汉书律历志》援引京房的话说:“夫十二律之变至于六十,犹八卦变至干六十四也。宓羲作易.纪阳气之初,以为律法。逮日冬至之声,以*钟为官、太簇为商、姑冼为角,林钟为征,南昌为羽,应钟为变富,蕤宾为变征。此声气之元,五音之正也。故各统一日。其余以次运行,当日者各自为官,而商费以类从焉。” 《礼运篇》:“五声,六律,十二管还相为宫北之谓也。以六十律分期之日,*钟自冬至始及冬至而复,阴阳寒燠风雨之占生焉。于以检摄群音,考其高下,苟非草本之声,则无不有所合。” 这些话把他发明六十律的目的讲的非常清楚,本来采用六十律相生法,当升到五十三次(即第五十四律)时,已与出发律极为相似,可以周而复始了。可是,焦延寿、京房为使律与历相结合,一定要凑成六十这一整数,即要使在六十律内达到象“以六十律分期之日,*钟自冬至始及冬至而复。”那样的还相为言。 其中六十律中的每一律或对应于一天,或对应于五天、六天、七天,八天等,在六十律轮过一周时。恰合天,从面可以形象地表达阴阳递互消长,五行相推制衡周爵复始的宇宙法则内涵。可见京房之六十律完全是籍律目之学以完成其易学及天文历法研究为宗旨的。 将十二律吕这些竹管按照方位置于室内案上。冬至日与气相应的那一根就是*钟。冬至这一天阴气到达极点,而一阳来复,为地雷复卦。对应*钟律管中的灰会飞出来,代表冬至日到了。冬至日本是自然界的客观现象,地球位于近日点。通常观测冬至日是看土圭影最长的一天,将其定为冬至日。而这种将律管与冬至阳气相应,并把*钟确定为标准音和起始的思想,体现了古人天人合一的观念。将十二律吕与五行和节气等相配,则是以数和阴阳五行思想作为基本延伸,扩大了范围。 《国语》:王将铸无射,问律于伶州鸠。对曰:“律所以立均出度也。古之神瞽考中声而量之以制,度律均钟,百官轨仪,纪之以三,平之以六,成于十二,天之道也。夫六,中之色也,故名之曰*钟,所以宣养六气、九德也。由是第之。二曰太蔟,所以金奏赞阳成滞也。三曰姑洗,所以修洁百物,考神纳宾也。四曰蕤宾,所以安靖神人,献酬交酢也。五曰夷则,所以咏歌九则,平民无贰也。六曰无射,所以宣布哲人之令德,示民轨仪也。为之六间,以扬沉伏,而黜散越也。元间大吕,助宣物也。二间夹钟,出四隙之细也。三间仲吕,宣中气也。四间林钟,和展百事,俾莫不任肃纯恪也。五间南吕,赞阳秀也。六间应钟,均利器用,俾应复也。” “律吕不易,无奸物也。细钧有钟无镈,昭其大也。大钧有镈无钟,甚大无镈,鸣其细也。大昭小鸣,和之道也。和平则久,久固则纯,纯明则终,终复则乐,所以成*也。故先王贵之。” “王以二月癸亥夜陈,未毕而雨。以夷则之上宫毕,当辰。辰在戌上,故长夷则之上宫,名之曰羽,所以藩屏民则也。王以*钟之下宫,布戎于牧之野,故谓之厉,所以厉六师也。以太蔟之下宫,布令于商,昭显文德,底纣之多罪,故谓之宣,所以宣三王之德也。反及嬴内,以无射之上宫,布宪施舍于百姓,故谓之“嬴乱”,所以优柔容民也。” 《乐纬》云:“玄戈,宫也,以戊子候之。宫乱则荒,其君骄,不听谏,佞臣在侧;宫和,则致凤凰,颂声作。”又云:“弁星,羽也,壬子候之。羽乱则危,其财匮,百姓枯竭,为旱。”即以宫音配玄戈,主君;以羽音配弁星,主物,将五声、五星和五*等杂糅在一起,并通过“戊子候之”。 《乐纬》还强调圣人作乐始于“天气”(天气为万物之本,能调礼乐,明教化,合五行而为一),故《乐动声仪》载:“作乐制礼时,五音始于上元,戊辰夜半,冬至北方子。”认为制礼作乐,起于戊辰夜半冬至的子时。据郑玄注:“戊辰,土位。土为宫,宫为君,故作乐尚之,以为始也。夜半子,亦天时之始。《礼稽命征》:‘起于太素十一月阏逢之月,岁在摄提格之纪。’” 首先,戊辰处于土位,而土位于五音中属宫,为君之象,象征制礼作乐的主体是“圣王”。其次,冬至夜半子时为天气之始。中国古代历法,往往将夜半作为一日之开始,朔旦作为一月之开始,冬至作为一年之开始。若这一年再有日月合璧,五星联珠的祥瑞,就可以定为上元。故古人十分重视这一时刻,在*治上被当作“考 终始”之期。再者,冬至处于仲冬,又是*钟律气产生的时刻:“仲冬日短至,则生*钟。”,*钟于十二律为律母,其他乐律都是由*钟律所生。所以这一特殊时刻,对圣王作乐而言,是非常重要的,既是新王受命开始之期,又是制礼作乐开始之时,而且其中还包含了汉代的卦气律气思想和星占术数学说。解释路径的差异,正反应了《乐纬》在接受《乐记》学说体系的同时,又进行了新的学理建构,将礼乐制作的根本导源于天道历数。 《律历融通》*钟配卦图 十二律吕配时图 四、律历合一思想下的具体产物——《太初历》 最初的律历合一的产物是《太初历》,《太初历》是中国历史上 部以国家之力组织编纂的历法,制定于汉武帝太初年间所以名为太初。其前的*帝历.夏历、殷历、周历、鲁历、颛项历,统称“古六律”,因为古四分历中的颛顼历误差越来越大,所以在太初元年由太史令司马迁、大中大夫公孙卿、壶遂建言改历,邓平和来自民间天文家唐都、落下闳等二十余人提出18种方案。 选定了邓平、落下闳方案。唐都测定28宿距离,落下闳作具体运算。太初历以又/日为回归年长度,29又43/81日为朔望月长度。西汉末年,又由刘歆修订改为三统历。 据《汉书律历志上》载,《太初历》计算以及和乐律关系如下: “律容一龠,积八十一寸,则一日之分也。与长相终。律长九寸,百七十一分而终复。三复而得甲子。夫律阴阳九六,爻象所从出也。故*钟纪元气之谓律。律,法也,莫不取法焉。” 太初历这里的律容指的就是*钟管的容积为八十一寸,*钟管长九寸,故而定日法为八十一也就是43/81.由此可见,太初历的参数是以标准*钟律龠为依据的。*钟律龠在《汉书.律历志》中称其为“律嘉量龠”,其“幂百六十二分,深五分,积八百一十分,容如*钟”。两龠为一合,十合为一升。但是,就容量而言,“深五分”就是长度为五分。而秦汉时代,标准*钟律长取为9寸。 蔡邕《月令章句》说:“*钟之管长九寸,孔径三分,围九分。”也就是说,律龠长l=9寸,内径d=3分,由此计算,律龠容积,此数值并不等于81。由此看来,上文的 句即“律容一龠,积八十一寸”就错了。这里的“积”自然是指律龠的容“容积”。“与长相终”即是将一日之长分为81分,“81”与一日之长相等。 第三、四句写成数学式为: 9x19=,+9=,÷3=60。这两句是证明*钟律9寸和19年7闰的关系。第五句的含义是,*钟长9寸,林钟长6寸;而*钟属“乾”卦,“乾”为天统、为阳、卦数为“九”;林钟属“坤”卦,“坤”为地统、为阴、卦数为“六”。六九代表阴阳,也对应冬至日和夏至日,因此说,“夫律阴阳九六爻象所从出也”。 现在看来,《易经》八卦中爻象也出之于律,体现了律和易数的配合,也为刘歆日后沿用易数讲历打下了基础。第六句“故*钟纪元气之谓律”的“纪”是梳理、整理之意;“纪元气”就是将元气中阴、阳二气分出来。在他们看来,这是*钟律的功能。这种思想正是后来产生“候气”的理论根据。由是,乐律便成了历法、度量衡、和八卦的起源。 实际上,《汉书.律历志上》的那段文字,只能表明太初历的制定者是将一日之长分为81分罢了。如同今日将一日分为24小时一样。但是,他们为了找到一个合乎天理的理由,便抬出了*钟律数,它的长度为9,9自乘是81。《汉书.律历志下》记载:“日法八十一。元始*钟初九自乘,一龠之数,得日法说到“*钟初九自乘”,本来就可以了,没必要再说。却偏要将9x9=81说成是*钟律龠的容积数,本来是打算附会上律数,然而没想到的是数据是错误的。然而,无论如何,这段历史记载表明,太初历的起算数据是以乐律数字为参数的。 邓平、落下闳还算出朔望月、回归年的长度。其中,9x9=81是他们最为在乎的数字,因为它可以直接和*钟之数扯上关系,也同样因为81可以和实际观测到的数据相对应。《汉书.律历志上》日法:“一月之日二十九日八十分日之四十三。先藉半日,名日阳历;不籍,名日阴历。所谓阳历者,先朔日生;阴历者,朔而后月乃生。” 由此可见,太初历一月之长,即朔望月=29又43/81日。这就是阴历月的天数;若借半日,即40.5/81日,则为30又2.5/81日,此为阳历。又据十九年七闰法,则一个回归年长度为: /19=.日(现在为.天,较为接近) 由此可见,日、月、年的长度数值都含有数字81。这部历法在当初被称之为“八十一分历”是名副其实的。后人省略其“八十一分”,简称“律历”。这就是中国文化史上特有的“律历”一词的由来。 史籍所载“以律起历”的原始内涵实际上就是以*钟律长9寸自乘作为历法“日”的基本参数。据《汉书.律历志上》载,落下闳、邓平所造“八十一分律历”完成后,于太初二年诏司马迁采用,并由国家颁布为“太初历”。宦者淳于陵渠派众人以观测天象证明它为当时最密合的历法,邓平也因此晋升为太史丞。27年之后,即汉昭帝元凤三年,太史令张寿王诘难太初历。张寿王提出太初历阴阳不调,冬至时刻“亏四分之三日”,并将此升为“乱世”之象。由此其实可以看出历法准确的重要性,轻则天时不准,气候不常,灾异横起。重则影响*治,如宋朝时期频繁更改历法,而准确性又并不高。导致周边使用宋朝历法的附属国家逐渐对宋朝失去了恭敬之心,甚至派使者嘲讽。 此时的汉昭帝见到历法出错严重,心中自然惶惶。于是立即下令核验,由主历使者鲜于妄人质问张寿王,由大司农中丞麻光等20余人对“日月晦朔弦望、八节二十四气”进行天文观则。经过三年观则,即在元凤六年,证明太初历仍是当时合天象的历法。从太初元年到元凤六年,太初历经过约30年几次大争论和观测实证而受到检验,真可谓“积三十年,是非乃审” 五、律与历的集大成者——三统历 太初历运用百年之后,它与天象观测的误差已经显露。西汉末,王莽持*,太中大夫刘歆受命“典儒林史卜之官,考定律历经过他修订后的太初历更名三统历。三统历的起算数目仍是邓平、落下闳的“八十一分历”不过,刘韵本身是汉代古文经学创始人,新莽时期被王莽尊为国师。他通晓各种数字并能运用其时经学中各种概念,也善于制造种种牵连附会或对应。在历法修订过程中那些数字对应阴阳五行和易数、律数,只不过是在于显示他的非凡学识而已。因此,在他写下的修历奏本中,制造了 的复杂的数字神秘主义。他提出所谓“天数”、“地数”,假托《春秋》、《易》数、大衍之数,推月法,将五星周期和月,年、闰的一系列数值附会于十二乐律和五行生克上,如此等等。 《三统历》的主要内容是运用“三统”解释历法。刘歆说:“三统者,天施、地化、人事之纪也。”《周易》乾之初九,音律*钟律长九寸,为天统;坤之初六,林钟律长六寸,为地统;八卦,太簇律长八寸,为人统。刘歆的《三统历》采用太初历的日法八十一,并说:“太极中央元气,故为*钟,其实一龠,以其长自乘,故八十一为日法。” 至于一个朔望月的日数,刘歆根据《周易·系辞上传》所谓“大衍之数五十,其用四十有九。分而为二以象两,挂一以象三,揲之以四以象四时,归奇于扐以象闰,五岁再闰,故再扐而后挂”,说:“元始有象一也,春秋二也,三统三也,四时四也,合而为十,成五体。以五乘十,大衍之数也,而道据其一,其余四十九,所当用也,故以为数,以象两两之,又以象三三之,又以象四四之,有归奇象闰十九,及所据一加之,因以再扐两之,是为月法之实。”用算式表达: {×2×3×4+19+1}×2=2,,÷81=29又43/81日、÷81=/81日,这就一个朔望月的日数。按照十九年七闰,所以,(19×12+7)×29又43/81÷19=/=又/日,这就是一回归年的日数。 刘歆又根据《周易·系辞上传》所谓“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天数五,地数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天数二十有五,地数三十,凡天地之数五十有五,此所以成变化而行*神也”,说:“并终数为十九,《易》穷则变,故为闰法”;“日法乘闰法,是为统岁”,即:(9+10)×81=年=日 “三统,是为元岁”即:×3=年 由于干支记日法60日为一周期,一统的日数,除以60,余数为40,所以,若以甲子日为元,一统后为甲辰,二统后为甲申,三统后才又到甲子,因而三统为一元。刘歆说:“历数三统,天以甲子,地以甲辰,人以甲申。” 在这一基础上,刘歆根据《周易·系辞上传》所谓“四营而成易,十有八变而成卦”,说:“阴阳比类,交错相成,故九六之变登降于六体。三微而成著,三著而成象,二象十有八变而成卦,四营而成易,为七十二,参三统两四时相乘之数也以阳九九之,为六百四十八,以阴六六之,为四百三十二,凡一千八十,…八之,为八千六百四十,……又八之,为六万九千一百二十,天地再之,为十三万八千二百四十,然后大成。”用算式表达: {×8×8}×2=,接着,“以乘章岁,为二百六十二万六千五百六十,而与日月会。三会为七百八十七万九千六百八十,而与三统会。三统二千三百六十三万九千四十,而复与太极上元”,也就是万古历法坑——上元积年法。用算式表达:×19×3×3=年“太极上元”实际上是5,元的大周期。 《三统历》在运用“三统”解释历法时,还涉及历法理论,有节气、朔望、月食及五星等的常数和运算推步方法,还有基本恒星的距度。与以往的历法相比,《三统历》包含了不少新的内容。它提出了所谓“朔不得中,是为闰月”的无中置闰法。还提出了以个朔望月为交食周期,期间共有23次月食,并且提供了计算月食发生月份的方法,此外就是《三统历》中测绘的五星行度和会合周期的精度有明显提高。 《三统历》和刘歆本人因为提出的“上元积年法”和“以律起历”的思想在后世经常被抨击,其中上元积年法更是给后世历算家带来了无穷无尽的噩梦。至于抨击“以律起历”的思想是因为这种将两个毫无关联的事物,借由神秘思想联系到一起。违背了历法以实际数据为本的本质,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刘歆本人虽然借由律均布到万物的这种思想起历数,但是他的数据本身却是较为合理的,是建立在观测之上的,即29又43/81,虽然附会了律数、易数但是并没有反过来影响到历法本身数据,只是以数学游戏强行给《三统历》附会上了神秘意义。 六、朱载堉《律历融通》思想 自汉朝以后,律历志似乎成为了官修史书中必备项目之一。而后世之人对于它的态度也是褒贬不一,下面我们来说一个赞同律历合一思想的代表性人物——朱载堉 朱载堉并非草头出身,我们单从他的姓上就能看出端倪,明朝的朱姓可是皇姓,而朱载堉正是太祖朱元璋的第九世孙。朱载堉年仅十岁的时候就已被册封为“世子”,顺理成章的成为朱厚烷(郑王)的继承者。朱载堉生在豪门,当属天之骄子。后世文学家曹雪芹的出身与朱载堉有那么几分相似,只不过,曹雪芹出身豪门,朱载堉则有正统的皇室血脉。虽说,上天给了朱载堉优越的出身,但他的成长中却充满崎岖坎坷。他父亲朱厚烷崇尚节俭,史籍记载:朱厚烷一辈子穿粗布衣裳,吃粗茶淡饭。虽说史籍中难免会有一些夸张的成分,但是,朱厚烷身为帝国王室,能做到作风节俭已经很难得了。朱厚烷的脾气十分耿直,甚至,有些“一根筋”,换做别人这样的性格本来是不错的。但是,现今活在皇亲国戚之中,耿直就成了要命的软肋。当时的皇帝朱厚熜沉迷于天道长生,寝宫中每日香烟弥漫,根本无暇顾及朝*。身为皇帝的兄弟,朱厚烷站了出来,上奏朱厚熜,请求兄弟别再将皇宫搞得乌烟瘴气。可能是朱厚烷的奏折太过直白,用词过于生硬,惹得朱厚熜心下不悦。心胸狭窄的嘉靖皇帝憋了两年,终于找到一个机会惩治了朱厚烷,不但将朱厚烷的爵位剥夺,还将他软禁在安徽。随着朱厚烷的失势,朱载堉一家就此败落。朱载堉过了十五年的世子生活就这样化为乌有,一家人沦落到一座破屋中艰苦度日。身为皇室成员,朱载堉既痛恨又无法发泄,无奈之中他找到了一个颇似现代“不抵抗主义”的法子,而且发誓:“父王一天不归,他一日不回宫。就这样,他在一间小土屋里一住就是十多年。”嘉靖皇帝驾崩后,隆庆继位,新皇帝赦免了叔父朱厚烷的罪状,朱载堉一家重回贵族阶层。此时的朱载堉已过了而立之年,虽说,生活水平重回 ,但此时的朱载堉却早已不是那懵懂少年。多年后,他逐渐成了与徐霞客、李时珍齐名的文化巨子,在音乐、物理、数学等领域取得建树。且完成《乐律全书》、《律吕正论》、《律吕质疑辨惑》、《嘉量算经》、《律吕精义》、《律历融通》、《算学新说》、《瑟谱》等重要书籍。单就音乐领域来说,时至今日,我们制造乐器和调音都使用一种“十二平均律”,发明这种技巧的正是仇富的愤青朱载堉。德国人赫尔姆霍兹是这样评价的:“听说有一个中国王子叫朱载堉,曾在无数守旧派音乐家的反对声中推行了新的音阶制度,至于将八度划分为十二个半音的技巧,也是这个中国人发明的。”流落民间的朱载堉在科学界也创造了惊人的奇迹,朱载堉现实设身处地的对古代度量衡进行了考察实验,然后,提出了一套行之有效的校正理论,优化了明朝的度量技术。朱载堉认为:当前(嘉靖年)的历法计算存在许多偏颇,在经过无数次的验算后确定了自己的观点,重新计算实验推出了新的历法计算公式。 许多现代数学家用高科技手段对朱载堉当时的公式进行了验算,结果表明,按朱载堉的公式计算出的年时间长度仅与今天相差17秒。这个结果一经公布在科学界迅速轰动,就连外国的科学家们都对此大感倾佩。更令人惊讶的是,古代并没有计算器,朱载堉仅凭算盘进行开方运算,研究出数列等式。纵观数学界,不论东西方都没有人比朱载堉更早解答等比数列中的首、末项。用朱载堉的方法,可以在不同进位制中进行小数换算。虽说,今天我们已有了更加科学高效的计算方式,但是,朱载堉的某些验算方法至今仍被数学界沿用。无数朝代曾将首都定于北京,如今,我们都知道北京的地理位置是东经°20′,北纬39°56′。那么,谁是 个将北京 定位的地理学家呢?还是朱载堉。 朱载堉一生中在许多领域中展现了非凡的造诣,放到现在朱载堉的每一次脑洞大开都会获得诺贝尔奖,堪称文化界的全方位人才。可以说,他成就震撼世界,连中外学者尊崇他为“东方文艺复兴式的圣人”。因此,朱载堉和郭沫若一起被列为“世界历史文化名人”。朱载堉的父亲朱厚烷过世后,按照明朝制度朱载堉原本是可以成为王爷的,可是,朱载堉却写了一封奏折,婉言拒绝继承郑王之位,一心一意投身在自己的事业中。 朱载堉在《律历融通序》中对于律历合一的看法是: “自落下闳造太初历,取法*钟律数”,而后知创数,而后知修历不可有所拘。”“历有五纬、七*,律有五声、七始,故律历同一,道天之阴阳五行一气而已。有气必有数有声,历以纪数而声寓,律以宣声而数行,律与历同,流行相生。*钟者,声气之元者乎。蕤宾、应钟是名“中”、“和”。所以济五音,和阴阳。旋宫之律可定声气之元,周流而不穷矣。故《周髀》曰:“冬至夏至,观律之数,听钟之音,知寒暑之极,明代序之化”,四是知律者,历之本也;历者,律之宗也。其数可相倚而不可相违,故日律历融通,此之谓也。万历九年正月吉日序” 这本书是他早期的著作,与他的另两部著作《律学新说》、《律吕精义》有所不同的是,《律历融通》既是一部律吕学专著,又含括了大量的中国传统天文历法内容。其前二卷主要叙述作者的传统历法研究成果,除全面继承了先秦以来的“律历合一”思想外,并有一套完整的历法体系,史称“*钟律历”,后二卷详细阐述了作者的“律吕学”思想,文中旁征博引间有辩驳,堪称上起远古下迄晚明的一部“律吕合一”学说之集大成者。这里朱载堉本身其实是支持刘歆这种律历相合的思维,认为律是历法之本。并且在《律历通融》中竭力用卦气、神历合一、律数、律母、律元、律象、律均、爻象等思想为律历志做解释,颇有孔颖达为董仲舒解释的意味。 朱载堉将其 之谓《律历融通》,是他尊崇秦汉圣贤确立的律历观念,即“其数可相倚而不可相违”的经典名句。但他的数字比附、或者说他的律与历彼此相“融通”的方式比起刘歆来要简单、直白得多。例如,他以万历九年()作为其*钟历的表面计算起点(实际计算起点年份为年之前年,即(年),是因为*钟9寸之故。这个起点他称之为“律元”,这个比刘歆提出的太极上元要简单明了的多。 他所谓“律母”是将一日之长分为百刻、一刻分为百分,以此对应的是*钟律横黍尺十尺之长,1尺=10寸=分;他的历年的实际起算点即年之前年,称为“律限”。因为乐律上有“纪之以三”之说,这个“三”与律母“百”相乘,即3x=。八度内十二律,五声十二律为六十调,他都在*钟历中作出相应比对。但他更多的是将历法中数字与《易》卦数相比附。正如他自己所说:“欲明律历之学必以象数为先”。他甚至将《易经》中卦爻之数全部抄录其著作的卷一之中,在后文还有专门的爻象章节。 律母百 七、后世对于律历志的看法 然而,前文最初提到了新旧《唐书》的作者们,未曾把律历二者合在一起做律历志。这是因为他们早就看出了前人造历中以数附会,牵强解释。 《新唐书.历志一》写道:“历法尚矣。自尧命羲、和,历象日月星辰,以闰月定四时成岁,其事略见于《书》。而夏、商、周以三统改正朔,为历固已不同,而其法不传。至汉造历,始以八十一分为统母,其数起于*钟之龠,盖其法一本于律矣。其后刘歆又以《春秋》、《易象》推合其数,盖傅会之说也。至唐一行始专用大衍之策,则历术又本于《易》矣。盖历起于数,数者,自然之用也。其用无穷而无所不通,以之于律、于《易》,皆可以合也。” 自汉到唐的八百年间,前人大都延续了《律历志》。这是历法家们 次在史书中指出了律数与历数合一是“附会之说”,作为正经的历法家大抵是实在看不下去这种积累多代的“糟粕”,故而提出了抗议。这无疑是中国历法史上一次突破和进步,打破了以往的禁锢。 然而尴尬的是,在《宋史,律历志一》中不但恢复了律历志,并且说:“古者帝王之治天下,以律历为先。儒者之通天人,至律历而止。历以数始,数自律生,故律历既正,寒暑以节,岁功以成,民事以序,庶绩以凝,万事根本,由兹立焉。古人自入小学,知乐知数,已晓其原。后世老师宿儒犹或弗习律历,而律历之家未必知道,各师其师,岐而二之。虽有巧思,岂能究造化之统会,以识天人之蕴奥哉!是以审律造历,更易不常,卒无一定之说。治效之不古若,亦此之由,而世岂察及是乎!” 这意思是,先吹捧了一下古代的帝王治理天下,都是以乐律和历法为先,儒家天人的思想,到乐律和历法就停止了。历法本身起始于数,而这种数源自于乐律,所以律历正确,寒暑时节就可以得知,万事根本就从此建立。古人(应当指的是汉朝)从小学开始就学习乐律和数学,早就晓本源。紧接着明嘲新旧《唐书》作者们不写律历志,是因为他们不懂律学和历法。他们不懂,是因为他们的“老师宿儒”没有学过律历之学,老师和学生都没文化,所以“不识天人之蕴”。 后来,清代的历算家梅文鼎先生在其著《历学答问》中对律历合志的历史事件评说道: “按律历本为二事,其理相通而其用各有别,观于唐虞命官羲和治历、夔典乐,各有专司。太史公本重黎之后,深知其理,故分为二书。班书(班固)合之,非也。后世言历者,率祖班志,故史亦因之,厥后渐觉其非而不能改。直至元许衡、郭守敬乃始断然以测验为凭,不复以钟律、卦气言历,一洗诸家之附会,故其法特精。此律历分合之由也。” 这算是对古代中国律历合一观念的流变所做出的历史总结,指出了律历合一思想的起源,以及班固合并律历二书的不合理之处。如果综合考虑律历志所诞生的历史时代背景,我们会发现在汉代新朝前后,由于王莽篡位,迫切的需要证明自己的合法性,所以这个时期的阴阳五行学说、符瑞、谶纬、灾异论等是高速发展的,在这种神秘思想和*治需求下,可以均布万物的律法就与百姓日用而不知的历法相结合,从而诞生了刘歆集大成的三统历。并且深深的影响到了后世王朝,至此封建社会的神秘主义下所诞生的律历合一的思想,可以就此盖棺了。归根究底,律历志的不合理之处在于将两个毫无关联的事物用神秘思想通过数学法则强行捆绑到一起,刘歆的数学固然高明,且学识渊博。但是他所留下的上元积年法和易数历数律数三合一的思想,给后世带来了不少难题。作为一个真正的历法家,应当以实际观测到的天文数据来制定历法,而不是将其玄之又玄,是应当像祖冲之说的一样:“愿闻显据,以核理实。浮词虚贬,窃非所惧”,幸运的是这种律历合一的思维,在千百年后的今天已经成为了历史的点缀,让后人可以直观的了解到当时古人对于乐律和历法的看法 |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daxueteng.com/gjygj/8467.html
- 上一篇文章: 全唐诗大全集卷381550116
- 下一篇文章: 国产之光耗时五年打磨,它撕开了中国特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