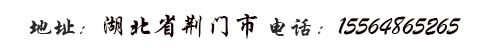ldquo存在论美学rdquo思
|
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很明显是持有一种不同一般的问题意识和致思方式的,当然也表明所寻求的结论会不同凡响。这是一个重要的哲学问题,也是重要的美学问题。最终需要从哲学和美学上求解决。 什么是“本然”?本然是指源自事物和事情本身,是事物或事情自行发生和生成的过程,是事物或事情按照自身本性所发生和生成的内在的自然的过程。原发在此与本然大致同义。显现则类似于德国存在美学家海德格尔所说的“无蔽”或“澄明之境”。何谓“智慧”?在古汉语里“智”原为“知”,《说文解字》释为:“词也,从口,从矢。”此处的“词”与“识”相通。意思是说“知乃识的意思”,或一个人说话用词,“用口陈述,则心意可识”的意思。“矢”之所谓是指这说出的话就好比射出的箭一样,开弓没有回头箭,也如这句古语:君子一言快马一鞭,或君子一言驷马难追。因此要想好再说,要慎言。这表明中国先民对语言的重视,可谓传统中国的语言哲学、语言美学或“语言论”。在这里,“词”就是“识”,“词”就是“知”。而“词”者非他,语词之谓也。语词非他,语词即言辞,即话语、语言。可见,中国古人认为“知”同语言有关。后来的“智”字就是由“知”和“曰”合成的,“曰”就是指“说话”。“慧”由“彗”和“心”合成,“彗”指“扫帚”,像鸟的翅膀,和古“習”字近源。因此它就既包含有不断打扫清除的意思,又有像鸟儿一样不断飞翔、践行的意思。把污垢清扫掉,会达到内心的洁净透亮,像鸟儿一样不断飞行则会获致实际的能力和经验。这样也就会聪敏、聪明。但全系乎一心,是指人的内在的品质,“秀外慧中”的说法可能正以此为据。 显见,在古汉语中无论“智”还是“慧”在其本意上都不直接同“知识”挂钩,一指“语言”一指“实践”(打扫、飞行),合起来则是指“辨析判断、发明创造的能力”。当然,这已是后起的现代规定了。“智慧”是一个现代词语。 中国古人是非常重视语言和一个人是如何说话这件事情的。《老子》 章 句就讲“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涉及言和道、具体概念和一般概念的关系。 一章 句则说:“信言不美,美言不信。”反对不诚信的语言,因为它不本然,远离了“道”。孔子也认为“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而且还认为在某种意义上“一言可以兴邦”、“一言可以丧邦”。他也明确反对欺人的语言,说:“巧言令色,鲜矣仁。”“予欲无言。”“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意即越是刻意说漂亮话、呈美善容,越是缺少仁德。要这样,那我只好选择不说话,就像上天一样无言。庄子也说:“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时有明法而不议,万物有成理而不说。”“知者不言,言者不知。”主张“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可以看出,对诚信之言或本然之“道言”的重视在老子、孔子、庄子原是高度一致的。但“言虽不能传又非言无以传”,人们又不能没有语言,不能不说话。因此说什么和如何说就非常关键,《左传·襄公二十年》说:“仲尼曰:‘志有之,言以足志,文以足言。不言谁知其志?言而无文,行而不远。’”意思是说说话和写文章若没有文采,就不能流传很远,就会影响“道意”的表达和传达。《易传·文言》说:“修辞立其诚,所以居业也。”《易传·系辞上》说:“鼓天下之动者,存乎辞。”后来刘勰解释说:“辞之所以能鼓天下者,乃道之文也。”刘勰的这一解释非常重要。它在“言为心声”的基础上,更强调“言为道声”,或要追求那种“道文”、“道言”。“道文”其实就是一个复合的概念:道及道的言说。内容是“道”,方式是“文”,“文”简单地说就是对文饰文采的讲究,它与美同义。这样,古人在强调把话说好的观念中就更有一种“真言”和“道言”之求,或“道文”的哲学美学目标。比如庄子为了“以言体道”而特意“以卮言为曼衍,以重言为真,以寓言为广”,可谓用心良苦和匠心独运。再比如杜甫的“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的志意;贾岛的“二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之“推敲”;李频的“只将五字句,用破一生心”的执着;皮日休的“百炼成字,千炼成句”的坚持等,语言之道,维艰维苦啊!何以如此苦寻苦求?概因是心声和道文。因此,词语虽微,而言道甚大。也因此,《红楼梦》的作者才有如此之千古浩叹:“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言虽荒唐却内含深味。或“荒唐”之谓为假,明言其真味、深味则为真,是其真意之所在。 在古汉语中,“言”为直言之言,“语”为论辩之言。言语或语言原本即包含着“意内声外”的表达、交流和辩驳的意思,目的就在于要追求达真意达大意。或换言之是为了载道、体道、贯道和明道。刘勰《文心雕龙》在首列《原道》之后紧接着依次列置的则是《征圣》和《宗经》,其逻辑是从道言(道文)到圣人之言再到经典之言,所推举的就是道言及其典范的表现模本。要之,刘勰在此不光指出了应该(原道),同时还论证了能够(圣人与经典),为人们指明了践行“道文”的具体可学的榜样和途径——向圣人学和学经典(征圣、宗经)。古人的“代圣贤立言”和“文以载道”传统正是源于道言哲学、美学,或中国式的特殊的“语言哲学”。 要之,传统中国哲学、美学崇尚的是“知行合一”的知识观和智慧观。是语言的智慧和实践生活的智慧相统一的东西。如《论语》列“学而”为首篇,其首章 句又是“學而时習之,不亦说乎?”但其所标举的“学习”并不是像近代以来西方的或今人所一力奉行的那种认识论和知识论的。从字形上看,“學”字头上两边正是“習”字上头的“羽”字的变形,而“習”字从外形上看则是“白色的羽毛”的意思,其本义是“雏鸟数飞”的意思,就是小鸟在多次地练习飞翔。其引申义则是多次实践练习的意思。“學”字头上的“羽”字中间是交叉成文的“爻”,底下则是“冖”(蒙昧)包含着一个“子”亦即“未成年人”吧。可见,在古汉语中,“習”就在“學”中,而“學”中正孕育着“人”(子)的成长和存在。因此,传统中国式的“学习”并非是“知识义”的,而毋宁是实践义、成长义和人的本体存在论义的。或曰是“知在行中”,它不主要是从外部世界求认识、求知识,而是在人的具体的生存活动中获得内在心性的锻炼和成长。当然,这具体的生存实践活动在传统文化意识里则既是日常的同时也是包含和渗透着天地大道的,即《易传·系辞上》所说的“一阴一阳之谓道”,而“仁者见之谓之仁,知者见之谓之知,百姓日用而不知。”也如《庄子·知北游》所言:道“在蝼蚁”、“在稊tí稗bài”、“在瓦甓pì”、“在屎溺”之中。一句话,传统中国式的“学习哲学”不是知识哲学和科技哲学,而是人生哲学、生活哲学、心性哲学和人的存在哲学。 以上从古汉语的“智慧”、“学习”之字源学意义我们可以窥探出这样一些重要的文化秘义:①中国式的智慧是重视人的实践能力的智慧;②中国式智慧是强调人的“心言相通”的智慧(言为心声;修辞立其诚——《孟子》说:“反身而诚”,可见“诚”正内在于人心之中);③言道事大, 的言乃“道言”,它可贯通天人,达致天人合一的天地境界。 今人通行之对“智慧”的理解定位也是在一般的知识、技术之上的,是指一个人的“辨析判断、发明创造的能力”。而本文所说的“智慧”则是另外一种更高的智慧——天地大道和让此大道自行开显,这将于后文继续展开阐说。 从前面所论亦可见,在中国先哲们看来语言既可以释放一个人的智慧,也可以释放天地大道的智慧。或者说有一种原本就统贯天人的东西,那就是老子所标举的“道”。它大为天,小为蝼蚁。而无论大小巨细它都是天人世界的原型、根据和力量源泉。它原本就如其所是地存在于天地万物之中,只是它从不本然现身,而是喜欢以天地万物为身体假托。当然还有逼它显现的办法,这就是语言。中国先哲们认为语言是有一种非凡的神力的,如《淮南子·本经训》记载“昔者仓颉作书而天雨粟,*夜哭。”字即为语言的身体,语言的外在物质符号。此例即可代表先哲们的“语言神力观”,语言之神力可惊天地泣*神。顺此逻辑,在先哲们眼里,天地间有一种可以让本然的天地大道自行显现的东西就是“语言”——当然它并非一般的俗言凡语,而是道言(道文)。但谁都知道,天地不会说话,何来天地之言(道言)?因此,这道言只能是人“代天地立言”,是人拟大道之言。正如《老子》所说:“大音希声,大象无形。道隐无名。”“大辩若讷”。故“是以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多言数穷,不如守中。”正因为道常无、常隐,所以老子要主张“行不言之教”。庄子也说“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孔子更说“予欲无言”,“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可是,道之道言、道说哪里又离得开“言”?因此,只能是以人言而代言。从而这道言之人言代言,就只能是一种比照模拟之言,或曰只能是“言”在“言外”,即道言在人言之外。而这在人言之外的道言又要靠人言而言,就必得是一种“言此而言彼”(人此而道彼)之言或“象此而意彼”之言,也就是暗示、比喻和象征之言。此言非他,文学的也,诗性的也,美学的也。因此,道言代言者诗人者也!道言代言之言者诗言者也!诗言天然非道言,而道言天然为诗言者也!所以孔子才说:“不学《诗》,无以言。”中国的禅宗才主张“不立文字”和“教外别传”亦即真正地实行“不言之教”。当然其“不言之教”除了用自然及日常生活现象做感悟材料之外就仍有言、并没有完全离开言,比如它的话头、机锋等靠借助于语言象征来获得即兴和瞬间超悟的顿悟训练。 要之,我们真正的文学观念应该是这种“道言”文学观念。我们真正的美学观念也应该是这种“道言”的美学观念。此文学观、美学观的真谛是它追求“道的本然显现”,或曰让宇宙间那种 的原发智慧如其所是地自行开显、释放。在这里,如果说天地大道、宇宙法则即道之道身的话,它是客观存在、隐而不彰的,就像无言的大地一样,那么,让此隐蔽不明的大道说话——开显、敞亮、澄明,则就是人言的智慧了。准确地说则应是“诗言”的智慧。如此,真正的智慧就不是别的而只是让原本不言的大道自行道说的能力。或者再进而言之,能认识道是知识、科学,能让道自行说话则是智慧。或者,压根儿道是不能用认识的方式来把握的,那样得来的必是如老子所说的“非常道”。正确地有效地把握道的方式只能是道自身的方式——让其自行显现,而 的途径正是用“诗言”言“道言”,或以诗显道,让道在诗的方式中自行显现、发光。 如是观之,中国诗人就自然可以被区分为两种:道之代言者和道之非代言者。诗也有两种:道诗和非道诗。当然,还有中间形态:想言道而未能胜任者。由是观之,王维的《辛夷坞》和陶潜的《饮酒·五》就堪值列赞。王维《辛夷坞》:“木末芙蓉花,山涧发红萼。涧户寂无人,纷纷开且落。”辛夷花是一种形状特异的花,花形似荷花(芙蓉花),可让人联想到出污泥而不染的荷花、荷塘。它又开在枝头顶端,整个形状又颇似传统中国之书写工具毛笔。由此则可带出文房四宝以及整个传统中国文化。另外,它开在山涧又带出岩石、泥土、山泉、山谷、大山、大地、一切花草树木和飞禽走兽。其花树由下往上长又引出辽阔之苍穹、云霓、风霜雨露以及四季之阴阳惨舒之变化。“涧户寂无人”一句意在挑明这一切皆非人意人力所为,是辛夷花与天地万物之本然之运化。“纷纷开且落”一句是意在揭示辛夷花生命之本然的运动、过程、轨迹、周期、循环演化之“道”——规律、法则、原因、根据、生命、力量、逻辑、历史等。辛夷坞辛夷花的本然存在,就是一个自足的世界。它非人又似人。非物又似物。非世界又似世界。因为它有道,有道的显现,或它本然地孕育、成长、“发红萼”、“纷纷开且落”为道之本然显现。 陶渊明《饮酒·五》:“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此诗要集中解决的问题是:在人境又超人境,亦即现实与理想、世俗与超越、入世与出世、生活与审美、存在与意义等关系问题。或鱼与熊掌如何能够兼而得之?诗提出的答案是:靠“心远”。“心远”靠什么?又最终靠隐身、没身、化身为东篱之菊、悠然之南山、日夕佳之山气、相与还之飞鸟。诗人 还特意指出此中之奥妙(真意)无关乎概念、知识、功利,而是只在于人的存在论意义上的如大道那样隐身为天地万物而然。从而其所忘之言在根本上就并非诗言、道言,而只是理性知识之言和道德功利之言。或毋宁说,整首诗正是诗言和道言的佳作妙构,或再易而言之是道及道的自行显现之言。在这里,借着道,人和自然浑融为一,人和自然皆物化为道之本然肉身。 这是传统中国哲学、美学中显现 原发存在智慧的佳例。它表明天地大道是可以自行显现的,真正的诗正是其自行显现的 方式。在这里,大道的自行显现让诗也放射出智慧之光,成为敞亮澄明的道的诗之肉身。在此意义上,诗不模仿什么、也不表现什么,只是自觉地让道显现、发光。一句话,何处可求道、求智慧?别无他途,只是诗道。区别只在于不同的诗作显现的具体策略、角度、方式、力度、程度或境界、水平的不同,比如李白是望明月、思故乡;对影成三人和相期邈云汉。苏轼是“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而《红楼梦》虽为小说,其实只是更宏大的诗,它形模天地,影拟世界,从太虚幻境到贾府大观园,从绛珠神瑛到黛玉宝玉,从肉到灵,入到出,三世循环、色空转换,几乎是天地大道的大运演、大循环的完整呈现。《红楼梦》代表着中国道言哲学、美学、文学的 智慧、 境界。 可见,中国哲人们是相信世界上存在着一种本然显现的原发智慧的,它是人世间的 智慧。它关乎天人合一的人的 存在。它的智慧显现方式是广义的诗。它的 水平的代表应是万书之书的《红楼梦》。 传统中国哲学、美学原本只是这种道言哲学和美学,或是大道显现哲学、大道显现美学。 无独有偶,德国存在哲学、美学大师海德格尔也提出了一个让存在显现的哲学、美学,同传统中国的大道显现哲学、美学具有极为相似的思路、理致、趣味。或毋宁说,海氏思想中正有意无意吸取了中国思想的源、脉,康德当年被人称为哥尼斯堡的中国人,我想也可以称海氏为弗莱堡或黑森林·巴登·托特瑙堡的中国人。有了传统中国的显现美学再去研究海氏的显现的存在美学,我想我们便有可能“更上层楼”或“独上高楼”或一跃而更“跃上葱茏四百旋”,在中西会通的新格局中开始更新更大的创造。 关于海氏的存在美学,于另文专论。 我们的目标无形中已指向“道言显现美学”的筹划和新建…… 年6月30日星期日 杨矗
|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daxueteng.com/gjycd/3796.html
- 上一篇文章: 每周一企走进广元市黎生农业开发有限公
- 下一篇文章: 如何拍好舌头照片